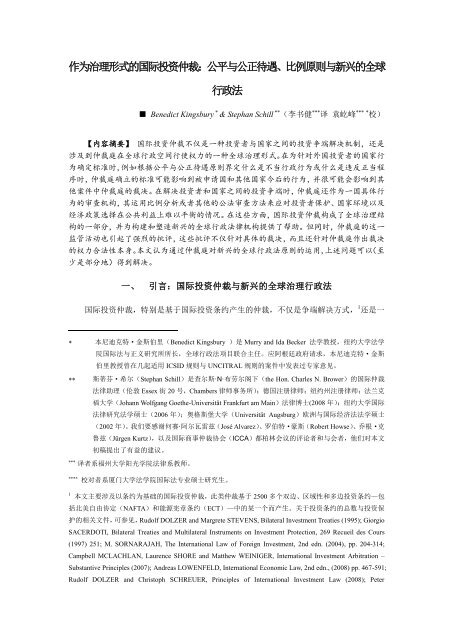作为治理形式的国际投资仲裁:公平与公正待遇、比例原则与新兴 ... - IILJ
作为治理形式的国际投资仲裁:公平与公正待遇、比例原则与新兴 ... - IILJ
作为治理形式的国际投资仲裁:公平与公正待遇、比例原则与新兴 ... - IILJ
Create successful ePaper yourself
Turn your PDF publications into a flip-book with our unique Google optimized e-Paper software.
作为治理形式的国际投资仲裁:公平与公正待遇、比例原则与新兴的全球<br />
行政法<br />
■ Benedict Kingsbury & Stephan Schill (李书健 译 袁屹峰 校)<br />
【内容摘要】 国际投资仲裁不仅是一种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还是<br />
涉及到仲裁庭在全球行政空间行使权力的一种全球治理形式。在为针对外国投资者的国家行<br />
为确定标准时,例如根据公平与公正待遇原则界定什么是不当行政行为或什么是违反正当程<br />
序时,仲裁庭确立的标准可能影响到被申请国和其他国家今后的行为,并很可能会影响到其<br />
他案件中仲裁庭的裁决。在解决投资者和国家之间的投资争端时,仲裁庭还作为一国具体行<br />
为的审查机构,其运用比例分析或者其他的公法审查方法来应对投资者保护、国家环境以及<br />
经济政策选择在公共利益上难以平衡的情况。在这些方面,国际投资仲裁构成了全球治理结<br />
构的一部分,并为构建和塑造新兴的全球行政法律机构提供了帮助。但同时,仲裁庭的这一<br />
监管活动也引起了强烈的批评,这些批评不仅针对具体的裁决,而且还针对仲裁庭作出裁决<br />
的权力合法性本身。本文认为通过仲裁庭对新兴的全球行政法原则的运用,上述问题可以(至<br />
少是部分地)得到解决。<br />
一、 引言:国际投资仲裁与新兴的全球治理行政法<br />
国际投资仲裁,特别是基于国际投资条约产生的仲裁,不仅是争端解决方式, 1 还是一<br />
本尼迪克特·金斯伯里(Benedict Kingsbury )是 Murry and Ida Becker 法学教授,纽约大学法学<br />
院国际法与正义研究所所长,全球行政法项目联合主任。应阿根廷政府请求,本尼迪克特·金斯<br />
伯里教授曾在几起适用 ICSID 规则与 UNCITRAL 规则的案件中发表过专家意见。<br />
斯蒂芬·希尔(Stephan Schill)是查尔斯·N·布劳尔阁下(the Hon. Charles N. Brower)的国际仲裁<br />
法律助理(伦敦 Essex 街 20 号,Chambers 律师事务所);德国注册律师;纽约州注册律师;法兰克<br />
福大学(Johann Wolfgang Goethe-Universität Frankfurt am Main)法律博士(2008 年);纽约大学国际<br />
法律研究法学硕士(2006 年);奥格斯堡大学(Universität Augsburg)欧洲与国际经济法法学硕士<br />
(2002 年)。我们要感谢何赛·阿尔瓦雷兹(José Alvarez)、罗伯特·豪斯(Robert Howse)、乔根·克<br />
鲁兹(Jürgen Kurtz),以及国际商事仲裁协会(ICCA)都柏林会议的评论者和与会者,他们对本文<br />
初稿提出了有益的建议。<br />
译者系福州大学阳光学院法律系教师。<br />
校对者系厦门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br />
1 本文主要涉及以条约为基础的国际投资仲裁,此类仲裁基于 2500 多个双边、区域性和多边投资条约—包<br />
括北美自由协定(NAFTA)和能源宪章条约(ECT)—中的某一个而产生。关于投资条约的总数与投资保<br />
护的相关文件,可参见,Rudolf DOLZER and Margrete STEVENS,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1995); Giorgio<br />
SACERDOTI, Bilateral Treaties and Multilateral Instruments on Investment Protection, 269 Recueil des Cours<br />
(1997) 251; M. SORNARAJAH,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Foreign Investment, 2nd edn. (2004), pp. 204-314;<br />
Campbell MCLACHLAN, Laurence SHORE and Matthew WEINIGE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br />
Substantive Principles (2007); Andreas LOWENFEL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nd edn., (2008) pp. 467-591;<br />
Rudolf DOLZER and Christoph SCHREUER,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2008); Peter
种全球治理结构。依靠公开的并得到广泛研究的裁决, 国际投资仲裁庭正在为界定全球行政<br />
法的具体原则和设定国家内部行政程序的标准提供帮助。 2 同样,当评价政府在投资者保护<br />
与其他重要的公共目的之间的平衡(即采用比例原则来分析)时,国际投资仲裁发挥着一种<br />
审查机制的功能。此外,仲裁庭对此类平衡作出的事后决定可能会影响之后的仲裁庭的行为,<br />
并且影响国家和投资者的预期行为。<br />
大多数仲裁员通常都是在这些投资仲裁的首要和直接的功能框架(即解决投资者与国家<br />
之间因涉外投资活动所产生的具体个别争端)内撰写裁决和公开评论的。但是,国际投资仲<br />
裁裁决的重要影响不仅限于针对特定争端中的当事方。在适用许多投资条约中措辞相似且语<br />
义宽泛的国际标准时,国际投资仲裁庭通过解释使这些标准具体化,并扩大或限制其含义,<br />
从而为大多数国家进一步界定了良好治理和法治的全球标准,这些标准被外国投资者用来对<br />
抗东道国。 3 仲裁庭还对更广泛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政策以及仲裁庭自身合法性和方法上的正<br />
当性有所解释,以此来审查国家的行为。<br />
仲裁庭加强或创立的标准,反映了公共权力行使中的一般原则,该原则不仅适用于国家<br />
行为,经过时间的推移和必要的变通还可适用于仲裁庭本身的活动。国际投资仲裁由此发展<br />
成为全球治理的一种形式。这些仲裁庭在全球行政空间内行使着权力。仲裁庭直接行使权力<br />
的范围包括:支持投资者或国家而作出的实体裁决,对事实作出的裁定,对法律意见书、费<br />
用和利息、时间、和解谈判需要的中止程序等相关事项作出的决定。更为根本的是,仲裁庭<br />
是作为一个整体行使着权力,他们影响指引国家行为的全球行政法律机构的发展,影响贸易<br />
法和人权等子领域中的习惯国际法和方法,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不同的投资者和公共利益间<br />
权衡,从而对公共政策与国家及投资者的未来行为产生影响。在公共或行政领域,任何重大<br />
权力的行使都要求其具备合法性。这不仅适用于仲裁庭和仲裁员,以及指定仲裁员的机构和<br />
仲裁撤销委员会的作为(或不作为),而且适用于国际投资仲裁制度这一整体。而对国际投<br />
资仲裁制度适用全球行政法,将成为解决合法性问题的关键因素。<br />
MUCHLINSKI, Federico ORTINO and Christoph SCHREU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br />
Investment Law (2008). 这类仲裁与纯粹基于合同的仲裁不同,后者适用的法律、东道国对仲裁的同意以及<br />
仲裁规则均取决于投资方和东道国的合同而非国际条约。尽管本文的焦点是投资条约仲裁,但许多观察结<br />
论经过适当修改也可以适用于那些完全独立于国际条约的、以合同为基础的国际投资仲裁。对于上述结论<br />
能否以及如何适用于纯粹的国际投资合同仲裁这一问题,本文不予论述。不过,一个有效的国际投资合同<br />
的存在可能对于本文中的条约分析与制度分析有修正性的影响。因此,国际投资仲裁庭如何处理投资条约<br />
仲裁中公法的含意,如比例原则的分析或公平与公正待遇的含意,较之基于东道国与投资者间的合同关系<br />
所涉及的程度有所不同。例如,国际投资合同通常针对缔约方相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有更为明确、详细的<br />
规则,这些合同对于条约规则以及习惯国际法的具体适用也可能有所指示。本文对这些问题不做论述。<br />
2 纽约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与正义研究所(<strong>IILJ</strong>)的全球行政法研究项目网站 www.iilj.org/GAL,该网站包含<br />
了一系列工作文件、大量的文献以及世界范围内其他学者文章的链接。该项目的第一批文献中有三本期刊<br />
论文集: Benedict KINGSBURY, Nico KRISCH, Richard STEWART and Jonathan WIENER, eds., The<br />
Emergence of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68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Summer-Autumn 2005, nos. 3-4),<br />
pp. 1-385; Nico KRISCH and Benedict KINGSBURY, eds., Global Governance and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in<br />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17 Eur. J. Int’l L. (2006) pp. 1-278; and the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symposium<br />
in 37 NYU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2005, no. 4). 由 <strong>IILJ</strong> 及其合作机构召开会议的文件等后续<br />
出版物包括:San Andres University in Buenos Aires, Res Public Argentina (2007-3), 7-141; University of Cape<br />
Town, Acta Juridica (2009); the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 in New Delhi (即将出版); Tsinghua Law School in<br />
Beijing (即将出版); and the University of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aw Review (即将出版).<br />
3 参见 David SCHNEIDERMAN, Constitutionaliz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2008).
国际投资仲裁是一个迅速发展的领域,基于 2500 多个双边投资条约(BITs)和一些重<br />
要的区域性条约,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东盟投资协定(ASEAN),每年有 300<br />
多件投资条约争端被公布且有许多新的仲裁被提起。 4 同时,国际投资仲裁也是一个脆弱的<br />
领域。一些国家在投资条约仲裁和投资条约保护方面变得日益谨慎。某些涉及阿根廷经济紧<br />
急状态的案件, 5 以及其他几个拉丁美洲国家政府所采取的立场, 6 凸显了对现有纠纷解决制<br />
度的适当性和合法性的顾虑。 7 传统的资本输出国,如美国,也越来越关注投资条约和投资<br />
条约仲裁对其监管权力所施加的限制。例如,美国关于 NAFTA 第 11 章的经验就对其近期<br />
的自由贸易协定和 BIT 谈判的态度有直接影响,并导致其 BIT 范本的修改。 8<br />
4 参见 UNCTAD, Latest Developments in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Dispute Settlement (2008) pp. 1-2,<br />
available at:www.unctad.org/en/docs/iteiia20083_en.pdf (记录了 2007 年底之前的 290 件投资条约仲裁)。<br />
5 例如,阿根廷司法部长Rosatti 在涉及阿根廷应对2001/2002 经济危机采取的紧急措施的首个案件(CMS Gas<br />
v. Argentina, 2005)败诉后说道:“我们仍坚持认为仲裁庭在该案中超越了权限,它没有准备好处理涉及单个<br />
国家的如此大量的案件,因为它有亲商的偏见,并且它没有资格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See BBC<br />
Monitoring Latin America – Political, supplied by BBC Worldwide Monitoring, 17 May 2005).<br />
6 2008 年 4 月 30 日,委内瑞拉通知荷兰表明其打算于 2008 年 11 月 1 日终止荷兰—委内瑞拉双边投资条约。<br />
Luke Eric PETERSON, ed., Investment Arbitration Reporter (16 May 2008), available online at :<br />
www.iareporter.com/Archive/IAR-05-16-08.pdf (报告说委内瑞拉援引“国家政策”为理由终止该条约)。玻<br />
利维亚于 2007 年 11 月 3 日退出了 ICSID 公约。 See “Bolivia Denounces ICSID Convention”, 46 ILM (2007)<br />
p. 973. 2009 年 6 月 12 日,厄瓜多尔国会进行了退出 ICSID 公约的投票。退出 ICSID 公约的讨论还见于尼<br />
加拉瓜、委内瑞拉以及古巴的相关报道。See Marco E. SCHNABL and Julie BÉDARD, “The Wrong Kind of<br />
‘Interesting’”, Nat’l L. J. (30 July 2007).<br />
7 关于这一方面的许多著作认为,国际投资仲裁中存在或者即将出现“合法性危机”,这由于各种不同的问<br />
题而产生,例如,争端解决机制的设计是基于临时仲裁以至于裁决不一致的风险随之产生,投资者的许多<br />
核心权利含糊、模棱两可,仲裁庭对其认为与投资无关的问题的无视行为。参见 Charles N. BROWER, “A<br />
Crisis of Legitimacy”, Nat’l L. J. (7 Oct 2002); Charles H. BROWER II, “Structure, Legitimacy, and NAFTA’s<br />
Investment Chapter”, 36 Vand. J. Transnat’l L. (2003) p. 37; Charles N. BROWER, Charles H. BROWER II and<br />
Jeremy K. SHARPE, “The Coming Crisis in the Global Adjudication System”, 19 Arb. Int’l (2003) p. 415; Ari<br />
AFILALO, “Towards a Common Law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How NAFTA Chapter 11 Panels Should Solve<br />
Their Legitimacy Crisis”, 17 Georgetown Int’l Envt’l L. Rev. (2004) p. 51; Ari AFILALO, “Meaning, Ambiguity<br />
and Legitimacy: Judicial (Re-)construction of NAFTA Chapter 11”, 25 Nw. J. Int’l L. & Bus. (2005) p. 279 at p.<br />
282; M. SORNARAJAH, “A Coming Crisis: Expansionary Trend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in Karl P.<br />
SAUVANT, ed., Appeals Mechanism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s (2008) pp. 39-45; Gus VAN HARTEN,<br />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and Public Law (Oxford 2007); Olivia CHUNG, “The Lopsided International<br />
Investment Law Regime and Its Effect on the Future of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47 Va. J. Int’l L. (2007) p. 953<br />
(认为现有的双边投资条约对投资者非常有利,而这些不平等现象将最终导致实施这些条约面临极大的困难<br />
); Naveen GURUDEVAN, “An Evaluation of Current Legitimacy-based Objections to NAFTA’s Chapter 11<br />
Investment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ss”, 6 San Diego Int’l L. J. (2005) p. 399.<br />
8 参见 Kenneth VANDEVELDE, “A Comparison of the 2004 and 1994 U.S. Model BITs: Rebalancing Investor<br />
and Host Country Interests” in Karl P. SAUVANT, ed., 1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Policy<br />
2008/2009 p. 283; Gilbert GAGNÉ and Jean-Frédéric MORIN, “The Evolving American Policy on Investment<br />
Protection: Evidence from Recent FTAs and the 2004 Model BIT”, 9 J Intl Econ L (2006) p. 357 at p. 363; Mark<br />
KANTOR, “The New Draft Model U.S. BIT: Noteworthy Developments”, 21 J. Int’l Arb. (2004) p. 383 at p. 385;
随着传统资本输出国日渐察觉自己将成为投资条约案件中的被告,他们对国际投资仲裁<br />
制度的批评也可能越来越多。可以预见的是,有些公司会在特殊情况下对西方国家经济的敏<br />
感部门进行投资并使其置于 BITs 的框架之下,这和他们在选择办厂地点时考虑贸易规则、<br />
在构建跨国经营时考虑税收政策的做法是一样的。通过对 BITs 的巧妙运用并引入一些扩大<br />
解释,仲裁庭已为特定 BITs 项下的投资指明了定义, 9 因此将海外公司置于 BIT 的保护之下,<br />
并据此使得投资者们能对传统资本输出国采取的措施提出挑战,将很可能使他们在西方国家<br />
拥有大量资产。因此,作为防范西方国家政府政策选择的有效保障机制,BIT 保护和国际投<br />
资仲裁会对私人经济主体越来越有吸引力。而动态的变化也应予以考虑。一些传统的资本输<br />
入国,如中国,现在也是对外投资(包括对西方国家投资)的主要来源,这些投资可能会受<br />
到传统资本输出国国内政局不稳定带来的不利影响。西方国家在应对 2008~2009 年金融危机<br />
时所采取的行动就推进了对投资条约问题更认真地思考。<br />
虽然判例法的发展日趋完善,但是一些裁决与决定在论证的质量方面还存在极大的不平<br />
衡,并且单个的仲裁庭无论如何也很难对系统层面的问题予以关注,因为他们的职责和首要<br />
义务是在个案中解决当事人的个别争议。因此,不同的仲裁庭作出了相互矛盾和相互冲突的<br />
裁决,这是由于仲裁庭本身的临时性以及缺少上诉或其他监督机制来保证法理上的一致性并<br />
加强投资条约仲裁的可预见性所导致的。 10 最后,机构性体系的结构、伴随着最惠国待遇条<br />
款所连结的无数双边条约以及修改多数重要多边公约时所需的全体一致同意要件也不便于<br />
其他主体对该体系进行改革。总之,上述改革所需的政治条件目前还并不完备。 11<br />
在现有国际投资仲裁制度结构所施加的严格限制内,一些呼吁改进的理论方法有很大的<br />
市场。这些方法包括:对一般国际法方法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VCLT)规定的条约解释<br />
方法的综合运用,对加强或补充了投资条约核心条款的习惯国际法予以深入分析和运用,对<br />
来自于完善的方法论中的一般法律原则进行大量参考,以及对经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及其他<br />
组织在“国际法的碎片化”问题上认可的系统性整合原则和技术的应用。<br />
Stephen SCHWEBEL, “The United States 2004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An Exercise in the Regressive<br />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3 TDM (April 2006). See generally Guillermo AGUILAR ALVAREZ and<br />
William W. PARK, “The New Face of Investment Arbitration: NAFTA Chapter 11”, 28 Yale J Intl L (2003) p. 365<br />
(讨论了发达国家在投资条约仲裁中作为被告的现象)。<br />
9 Cf. also Anthony SINCLAIR, “The Substance of Nationality Requirement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br />
ICSID Rev. – For. Inv. L. J. (2005) p. 357; Markus BURGSTALLER, “Nationality of Corporate Investors and<br />
International Claims against the Investor’s Own State”, 7 J. World Inv. & Trade (2006) p. 857. 例如在 Aguas del<br />
Tunari, S.A. v. Republic of Bolivia (ICSID Case No. ARB/02/3)一案的判决中, 仲裁庭在 2005 年 10 月 21 日对被<br />
告提出的管辖权抗辩做出决定(判决书第 206 段及以下),仲裁庭认为即使荷兰方只以投资设备的方法参与<br />
组建公司,此外再无实质性的联系,但是注册在荷兰的公司拥有科恰班巴(Cochabamba)的水利资源设<br />
施这一条件已足以使荷兰和玻利维亚的 BIT 得以适用。另参见 Stephan SCHILL, The Multilateralization of<br />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Chapter V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2009)。<br />
10 关于投资条约仲裁的相互矛盾及其制度和程序原因,参见 Stephan SCHILL, 同上,p. 281 et seq。 另见<br />
Susan D. FRANCK, “The Legitimacy Crisi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Privatizing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br />
through Inconsistent Decisions”, 73 Fordham L. Rev. (2005) p. 1521 at p. 1523。<br />
11 因此,ICSID 秘书处提交的一份改革建议几乎没有得到附和。参见 ICSID Secretariat, Possible Improvements<br />
of the Framework for ICSID Arbitration, para. 20 et seq., available at :<br />
www.worldbank.org/icsid/highlights/improve-arb.pdf。另见 Christian TAMS, “An Appealing Option? The Debate<br />
about an ICSID Appellate Mechanism”, 57 Beiträge zum Transnationalen Wirtschaftsrecht (2006)。
本文并不打算重复有关上述方法的大量文献。相反,本文表达的是一种互补的却被忽<br />
视的观点,即国际投资仲裁制度的薄弱不仅反映出该制度在设计与规划发展上的欠缺,也反<br />
映出其未能被置于涉及国家和公共利益的治理理论中。随着公共权力行使的理论与实践以及<br />
公共利益的表达不断发展,人们认为国际投资仲裁制度已经越来越不协调。本文认为:全球<br />
行政空间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却意义深远的方式,它对国际投资仲裁进行概念<br />
化,并使之与当前需要和未来趋向更加协调,而非唐突地试图完全改变现有的制度模式,该<br />
理论中全球行政法和法律公共性(publicness)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任何从根本上改变现<br />
有模式的尝试,除非是由于普遍的危机共识所引发的,否则不论其有何优点都必然要面对巨<br />
大的政治和经济困难。 12<br />
全球行政法的概念假定全球治理的大部分内容可以作为行政行为予以有效地分析。与那<br />
些截然分开(如私人、地方、国家、国家间)的监管层面不同,不同主体与层级的聚集构成<br />
了一个多样化的“全球行政空间”,它包括国际组织和跨国网络以及在国际范围内运作或引<br />
起跨境监管效果的国内行政机构。 13 传统国际法对“国际”的认识主要指“政府间”的,其<br />
在国内与国际之间存在着一条清晰的界限,而“全球行政空间”的观念则与之不同。在全球<br />
治理的实践中,由规则制定者、解释者和适用者组成的跨国网络打破了这种严格的壁垒。<br />
全球行政空间正日益被以下主体所占据:跨国私人监管者、混合机构(如涉及国家或国<br />
家间组织的公私合伙企业)、其行为有国际影响的国家公共监管机关(该影响可能不在中央<br />
行政权力的控制之下)、无条约(包括“自愿联盟”)基础的非正式国家间机构以及通过行政<br />
型行为影响第三方的正式的国家间组织(如联合国的机构)。很多全球治理的管理行为是高<br />
度分散的,而非十分系统化。在全球监管治理中一些实体被赋予它们不愿意或并非为其设计<br />
或准备的角色:仲裁员很可能将国际投资的一些仲裁庭归于此类。<br />
随着发展中的规制结构面临着透明度、磋商、参与、合理的裁决以及增强问责性的审查<br />
机制的要求,全球行政法正在逐步形成。这些要求及其回应越来越多的被制定成具有共同规<br />
范性质(特别是行政法律性质)的条款。有观点认为在前述问题中有些一致的适当原则和实<br />
践,这种认识对加强或者削弱不同治理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具有日益重要的影响。在考虑<br />
到这些现象时,有一种方法将全球行政法理解为法律机制、原则和实践,在社会认同的支持<br />
下促进或影响全球行政机构的问责性,其主要是通过确保这些机构满足充分的透明度、磋 商、<br />
参与、合理和合法标准,以及通过提供对这些机构做出的规则和决定的有效审查而做出的。<br />
14<br />
全球行政法涉及的是国家之外的机构以及各国以超出自身及其法律范围的方式行使公<br />
共权力的情况。 15 因此它至少在理念上引入了对公共性的要求。 16 在现代民主条件下,公共<br />
12 Cf. also VAN HARTEN, 见前注 7; Gus VAN HARTEN, “The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br />
Arbitration of Individual Claims Against the State”, 56 Int’l & Comp. L. Q. (2007) p. 371.<br />
13 Benedict KINGSBURY, et al., “Foreword: Global Governance as Administration”, 68 Law & Contemp. Probs.<br />
(2005, nos. 3-4) p. 1.<br />
14 Benedict KINGSBURY, Nico KRISCH and Richard STEWART, “The Emergence of Global Administrative<br />
Law”, 68 Law & Contemp. Probs. 15 (2005, nos. 3-4).<br />
15 Armin von BOGDANDY, “General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Authority: Sketching a Research Field”, 9<br />
German L. J. (2008) p. 1909.<br />
16 Benedict KINGSBURY, “The Concept of ‘Law’ in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20 Eur. J. Int’l L. (2009) p. 23.<br />
本段与前面三段借鉴了此处引用的文章。
性是法律概念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公共性以及相关的普遍适用性的质量是法律概念在民主<br />
法治时代所必须的。 17 据此,公共性主张法律必须由整个社会和公众制定,并且主张法律解<br />
决的应是社会本身所关注的问题。全球行政法之所以被称为“全球”而非“国际”既是为了<br />
避免其被误认为只是公认的实然法(lex lata)或甚至是应然法(lex ferenda)的一部分,<br />
也是为了包括更多不同的法律渊源,而不仅仅限于“国际法”的规范概念。<br />
本文论述的是在全球行政法项下理解国际投资仲裁的三种法律问题及其公共性的观点<br />
(第二部分至第五部分)。本文第二部分表明国际投资仲裁庭正迅速制定一套通用标准,并<br />
对这些标准作出示范性的适用,以此来应对国家行使行政权力影响到外国投资者的情况。由<br />
此,仲裁庭有助于确定国家良好行政行为的标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本文对两个受<br />
到特别关注的问题作出了回应。第一,仲裁庭从何处得到这些更详细的标准?在解释宽泛的<br />
条约标准(例如公平与公正待遇)时,条约解释的一般原则与法律分析需要得到比较行政法<br />
以及对国家如何进行良好行政的系统研究的支持。但许多裁决仅仅通过引用其他裁决(这些<br />
裁决自身的说理可能就很勉强)及仲裁员不严密的主观意见和经验来弥补缺陷。于是引出了<br />
第二个问题,即这些标准是在投资者申诉的有限范围内制定(或创立)的,其缺乏不同机构<br />
的积极参与,缺乏在不同背景下对于国家实施良好行政行为的现实定义,尤其缺乏与其他国<br />
家良好行政行为标准的协调,这些标准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就贸易有关的政府行为、国际人权<br />
法庭的相关判决、国际金融及援助机构在给发展中国家贷款或技术援助等背景下作出的要<br />
求。<br />
由于对环境方面的事项、劳工与社会标准以及经济危机中的政府管理或者其他有关全人<br />
类的重大问题缺乏回应,国际投资仲裁的程序和裁决必须面对和处理人们对这些方面的指<br />
责,本文第三部分就是解决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问题。阿根廷中止关税增长和比索兑换的紧<br />
急事件,玻利维亚在暴动后对 Bechtel 水利合同的取消,安大略省拒绝继续实施将多伦多的<br />
垃圾倾倒入湖的计划,或者是哥斯达黎加因为设立自然保护区而禁止某外商独资农场的发<br />
展,这些都是投资保护与公众关注之间相冲突的例子。为应对 2008 年~2009 年的全球金融<br />
危机而采取的救助、补贴与其他紧急措施也引发了同样的问题。在这些情况下,国际投资仲<br />
裁庭要对国家行使监管权力时所采取的措施与该措施对外国投资者所造成的损害进行权衡。<br />
然而,投资仲裁庭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所采取的方法与各种国际和国内法院所采取的方法相比<br />
有很大区别,而且相对简单。尽管许多国际人权法院以及许多国内法院经常常运用比例分析<br />
对权利与限制该权利的政策进行平衡,但是在国际投资仲裁中只有少量仲裁庭采用过这种方<br />
法。取而代之的是,仲裁庭对许多案件中所涉问题的复杂性和对抗性仅仅进行略微的分析和<br />
权衡,而这些案件往往需要更强大的分析方法,比如涉及影响现有外国投资者与国内主体的<br />
普遍适用的立法措施的案件,或者涉及行政机构依法行使自由裁量职能对外国投资者施加监<br />
管限制并因此对其造成特别损害的案件。第三部分研究了不同的争端解决机构在处理此类权<br />
利和原则冲突时所采取的方法。少数投资仲裁庭在处理投资保护与促进非投资利益相冲突的<br />
案件时会借助于比例分析,本部分对此进行了评价,并且认为在特定情况下这是国际条约法<br />
解释与适用所允许甚至是必要的组成部分。本部分继而表明,在应对必须通过法律评价来权<br />
衡的重要利益间的冲突时,仲裁庭除了采用与国内法院或其他国际法院、国际仲裁庭相类似<br />
的方法外可能别无选择。尽管运用比例分析方法可能存在严重问题(尤其是存在授予仲裁庭<br />
更多治理权力并对其提出更多苛刻要求的风险),但从长远来看,比例分析的适用是与一系<br />
17 Jeremy WALDRON, “Can There Be a Democratic Jurisprudence?”, NYU School of Law, Public Law Research<br />
Paper 08-35 (2008) available at :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br />
abstract_id=1280923&rec=1&srcabs=1299017。
列新兴的全球监管治理的公共法律原则相适应的。<br />
有一种观点认为作为一种全球治理形式,国际投资仲裁在其自身合法性以及新兴的全球<br />
行政法的规范性标准的要求方面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与其他机构在全球治理中行使权力的<br />
方式类似,国际投资仲裁在以下事项上要做到尽责:如机构的设置和仲裁员的指定与回避,<br />
文件公开的透明度,接收被裁决影响的团体的意见书,举行公开开庭,说明作出裁决的理由,<br />
遵循有效地审查程序等等。本文第四部分的第一节内容认为即使每一个机构有所不同,规范<br />
性考虑与法律原则是可以适用于各种跨国治理结构相交的范围内的。所有这些机构都涉及超<br />
越一国范围的公共权力的行使,而且大多数都是全球行政法的潜在制定者和主体,它们之中<br />
很多也是通过国际公共法律秩序的统一体连接起来的。 18 因此,单纯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内<br />
讨论这个问题是错误的,因为它与全球治理其他领域的规则与实践并非完全分离。坚持这些<br />
更广泛的规则,特别是习惯国际法与条约解释规则,以及新兴的全球行政法规则与国际公共<br />
权力规则,与解决国际投资仲裁中的合法性问题密切相关。本文第四部分的第二节讨论了这<br />
一宽泛议题中的一个方面,并明确指出:即使现行制度不做任何根本性改变,国际投资仲裁<br />
庭通过提高自身论证的质量以及裁决的一致性就可能使自己达到合法性的要求。<br />
国际投资仲裁制度有利于促进优化投资和有效地利用资源,这是一个标准但不充分的观<br />
点。在这个观点之外,本文的结论(第五部分)与国际投资仲裁制度的规范性依据这一根本<br />
问题联系起来。这些深层次依据可能包括民主的问责性和参与机制的增强,良好有序的政府<br />
管理水平的提高以及对于权利和其他应得利益的保护。国际投资仲裁的现有制度还不足以为<br />
其公共视角与治理视角的规范性依据正名。出于结构性的理由,为这些价值观念正名是一项<br />
公益事业。虽然重大的变革是必要的,但渐进式的改革也很有价值,并且这样的改革已在进<br />
行当中。新兴的全球行政法为此提供了重要的规范与实用的指导。<br />
二、 投资仲裁作为对国家行为的规制:“公平与公正待遇”理论<br />
如同在某些友好通商和航海条约中一样,各国向外国投资者提供“公平与公正待遇”的<br />
义务在现代的 BITs 以及关于投资的多边条约中是一个标准条款。 19 因此,对于一个迅速形<br />
成中的解释性说明机构和仲裁庭所作出的裁决而言,它已成为文本基础。在许多方面,这一<br />
理论借鉴或深入地结合了前几十年的习惯国际法材料和分析。因此,当前所谓的条约标准与<br />
习惯国际法相分离的争论,特别是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第 1105.1 条的争论,<br />
不应当掩盖条约与习惯国际法在标准和机制上的基本联系。 20<br />
18 Cf. Armin von BOGDANDY, Philipp DANN, Matthias GOLDMANN, “Developing the Publicness of Public<br />
International Law: Towards a Legal Framework for Global Governance Activities”, 9 German L. J. (2008) p. 1375;<br />
and Benedict KINGSBURY,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in P. CANE and M. TUSHNET, eds., The Oxford<br />
Handbook of Legal Studies (2003) p. 271.<br />
19 关于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的历史,参见 Stephen VASCIANNIE, “The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Standard<br />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Practice”, 70 Brit. Yb. Int’l Law (1999) p. 99。<br />
20 关于公平与公正待遇和习惯国际法项下国际最低标准之间关系的争论,参见 Rudolf DOLZER and<br />
Christoph SCHREUER,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2008) pp. 124-128; Andrew NEWCOMBE<br />
and Lluís PARADELL. Law and Practice of Investment Treaties: Standards of Treatment (2009) pp. 263-275;<br />
Campbell MCLACHLAN,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57 Int’l & Comp. L. Q. (2008) p.<br />
361。
但是,对于当前各国在外国投资的监管实践中出现的许多具体问题来说,国家责任与外<br />
交保护的传统结构以及在拒绝司法和正当程序等问题上固有的习惯国际法标准,可能还不够<br />
有效和细致。相反,习惯国际法、国家条约实践以及新增的许多国际投资仲裁庭作出的法理<br />
解释为国家行为(包括在某些方面影响外国投资者的纯粹的国内行政行为)制定了一套重要<br />
标准。这些标准难免与国家良好的行政管理联系更紧密,因为尤其是在开放的经济体系中,<br />
大部分行政行为普遍适用于每一个人,而非仅对外国投资者特别适用。公平与公正待遇理论<br />
因此成为当代公共行政理论的一部分。<br />
不过,一些对“公平与公正待遇”更为彻底的论述错误地认为它为国家行政管理建立了<br />
一个统一的全球标准,该标准与发达国家的行政法(或者关于某些方面的宪法性法律)是完<br />
全等同的,但其根本没有考虑到新兴的全球经济以及国家利益和环境的特殊性。习惯国际法<br />
标准是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的,该标准对实现投资条约的目的与宗旨帮助很大,尤其是有利<br />
于促进外国投资的流动,有助于为全球经济的运行构建一个法律机制。那些因为投机或者腐<br />
败原因导致国家公然干预外国投资者资产或经营的恶性案件,显然违反了此全球标准。许多<br />
这类案件都有典型的拒绝司法或者违反正当程序的情况,解决它们无需详细的解释性结构或<br />
者基本的治理分析。<br />
然而,“公平与公正待遇”这类国际投资法的抽象原则,可以用条约解释的一般原则来<br />
认定其已超越了一个统一的(但是适度的)传统最低标准,以便使其涵盖更严格的标准。同<br />
时,这些严格的标准还需要考虑有关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与具体情况,以及投资者和与投资有<br />
关的安排的情况。在这一方面,投资条约仲裁庭本身就是全球行政法面临的挑战的一部分,<br />
即形成比较与原则分析的有效技术,为充实一般原则的内容提供丰富的资源,并为将这些原<br />
则适用于与新兴全球社会要求相符的当地具体环境方面提供一套方法。这使得人们有可能解<br />
决以下情况:即一个公平与公正的严格标准不能确认某特定发展中国家在行政管理方面的持<br />
久能力和资源问题(这不会使一个精明的投资者感到惊讶)。处理这类情况的起点是在一国<br />
积极干预外国投资的案件、特定种类的不作为的案件,以及东道国行政机关对于投资者的请<br />
求作出不适当应对的案件之间做一个粗略的区分。<br />
解释和适用抽象的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涉及到《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关于国际条约法律<br />
解释的一种特定解释学,还包括对于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借鉴。为有关的机构、主体和问题量<br />
身制定这种解释学是必要的。这种解释学(至少对于较少的恶性案件和增加更多良好治理与<br />
良好行政的精细标准来说)可能需要运用比较的方法。该方法试图从国内法律制度以及国际<br />
法律制度中提取出一般原则,后者规定了政府或者其他公共权力在行政、司法与立法程序中<br />
的行使标准。本文第三部分将对比例分析的运用以及适用此类原则的相关方法予以探讨。而<br />
本部分旨在从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及全球行政机构在非投资领域的新实践中,尤其是在投资仲<br />
裁庭的实践中为“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的要素做一个概括。这样做是为了概括出某些具体<br />
要素,它们尤其适用于国家行政机关,并且对于全球行政法原则的进一步具体化也有影响。<br />
公平与公正待遇要素的五组规范性原则更为详细地出现在仲裁庭的分析中。 21 这些原则<br />
是:(1)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可预见性与一致性要求,(2)合法期待的保护,(3)对授予程<br />
序和行政正当程序以及禁止“拒绝司法”的要求,(4)透明度要求,以及(5)合理性与比<br />
例性要求。在很多国内法律体系中,这些原则作为法治概念的子元素或更广义上的表述同样<br />
占有重要的地位。人们可能将这些原则与其他国际机构针对公共权力在国内外行使上所阐明<br />
的相同渊源的原则联系起来,而且可能对这些相同渊源的原则产生进一步的影响。这种联系<br />
21 以下借鉴了 Stephan SCHILL,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under Investment Treaties as an Embodiment of<br />
the Rule of Law”, <strong>IILJ</strong> Working Paper 2006/6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Series), available<br />
at :www.iilj.org/publications/2006-6Schill.asp.
在一些习惯国际法的分析研究与国际法院和各类求偿委员会的一些重要决定中可以找得到。<br />
然而,在当前的国际投资仲裁中,人们还没有对这些原则更广的比较与规范依据进行充分挖<br />
掘。以下各部分将逐个对与五组原则相关的新近裁决进行研究,以便指出可能弥补上述缺陷<br />
的方法。<br />
(一) 稳定性,可预见性,一致性<br />
国际投资条约仲裁庭经常将公平与公正待遇与东道国法律体制的稳定性,可预见性和一<br />
致性联系起来。例如在“ CMS v. Argentina”案中,仲裁庭指出:毫无疑问…一个稳定的法律<br />
和商业环境是公平与公正待遇必不可少的要素。 22 关于调整外国投资者活动的法律体制的可<br />
预见性也受到了同样的重视。例如在“Metalclad v. Mexico”案中,仲裁庭基于墨西哥“未<br />
能够为 Metalclad 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确保一个......可预见的体制”这一理由,作出了墨西<br />
哥违反 NAFTA 第 1105.1 条的裁决。 23 同样,在“Tecmed v. Mexico”案中,仲裁庭指出:外<br />
国投资者需要“事先知道所有规范其投资的规则、法规、相关政策的各项目标、行政做法和<br />
指令,使其能够计划投资并遵守这些法规。” 24 一些仲裁庭补充说,法律体制缺乏确定性或<br />
过于模糊的规则可能违反公平与公正待遇原则。 25 同样,政府行为的一致性也在理论上受到<br />
重视。因此,在 Tecmed 案中,仲裁庭强调:为了符合公正与公平待遇,一个国家机构作出<br />
决策的一致性是必要的。 26 同样,在“MTD v. Chile”案中,仲裁庭基于“同一政府的两个<br />
机构针对同一投资者的行为之间的不一致性”,认为这违反了公平与公正待遇。 27<br />
总的来说,正如富勒(Lon Fuller)的“法律的内在道德性”(inner morality of law)所阐<br />
明的一样,这些观点体现了法律基本要求的几个要素。 28 许多国家的法律制度同样强调法律<br />
的确定性与法律的安全性,这或许在德语“法律的确定性”(Rechtssicherheit)中得到最强<br />
有力的实证。 29 法律规范性的核心是允许个人和组织调整自身的行为以便与法律秩序的要求<br />
22 CMS Gas Transmission Company v. The Republic of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01/8), Award of 12 May<br />
2005, para. 274. Similarly, Occidental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Company (OEPC) v. The Republic of Ecuador<br />
(UNCITRAL, LCIA Case No. UN3467), Final Award of 1 July 2004, para. 183.<br />
23 See Metalclad Corporation v.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ICSID Case No. ARB(AF)/97/1 (NAFTA)), Award of<br />
30 August 2000, para. 99.<br />
24 Tecnicas Medioambientales Tecmed S.A. v.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ICSID CASE No. ARB (AF)/00/2),<br />
Award of 29 May 2003, para. 154.<br />
25 例见 OEPC v. Ecuador, 见前注 22, para. 184 (批评了国内税收法律变化的模糊性,即其“对于其含义和<br />
范围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br />
26 Tecmed v. Mexico, 见前注 24, paras. 154, 162 et seq. 另见,OEPC v. Ecuador, 见前注 22, para. 184.<br />
Similarly, Ronald S. Lauder v. Czech Republic, Final Award of 3 September 2001, para. 292 et seq。<br />
27 MTD Equity Sdn. Bhd. and MTD Chile S.A. v. Republic of Chile (ICSID Case No. Arb/01/7), Award of 25 May<br />
2004, para. 163.<br />
28 Lon FULLER, The Morality of Law (1969). See KINGSBURY, 见前注 16, p. 23。<br />
29 在许多国内法律制度中,法治的这一方面主要被认为是一个宪法的标准,See for its implementation in the<br />
German Constitution Helmuth SCHULZE-FIELITZ in: Horst DREIER, ed., Grundgesetz – Kommentar, Vol. II<br />
(1998) Art. 20, para. 117 et seq.; see Richard H. FALLON, “‘The Rule of Law’ as a Concept in Constitutional<br />
Discourse”, 97 Columb. L. Rev. (1997, no. 1) p. 14 et seq. with references to US constitutional practice; more<br />
generally, 另见 Joseph RAZ, “The Rule of Law and its Virtue”, 93 L. Quart. Rev. (1977) p. 195, at p. 198。
相适应并形成稳定的社会和经济关系。这是大多数法律制度的初衷,在发达资本主义制度民<br />
主条件下尤其如此。国际法和全球治理的法律机构很可能促进并实现这一初衷。<br />
然而,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不能也不应该意味着法律体制将永恒改变,也不意味着其自身<br />
能够为投资项目提供一个商业保证。 30 同样,国内监管体系也不可能完全消除不一致性。 31 此<br />
外,每一种法律秩序的稳定性程度将因为每个国家所面临情况的不同而不同,并且这种矛盾<br />
的性质也可能不同。同样,与正常进程中的公共权力运用相比,在严重的危机或紧急情况下<br />
可能需要不同的反应。 32 因此,稳定性、可预见性和一致性必须基于具体案件的情况予以实<br />
现。<br />
(二)信赖与合法期待的保护<br />
在“Saluka v. Czech Republic”案中,仲裁庭认为合法期待概念是“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br />
的主要要素。” 33 这个概念以不同的形式在许多国家法律制度中, 34 或在一般国际法中出现。<br />
35 该概念的主旨是对信赖的保护,以对抗某种行政和立法行为。因此,在“Tecmed v. Mexico”<br />
案中,仲裁庭认为公平与公正待遇要求“应当向国际投资提供的待遇不会影响到外国投资者<br />
进行投资时所考虑到的根本期待。” 36 同样,在 International Thunderbird Gaming Corporation v.<br />
30 See Emilio Agustín Maffezini v. The Kingdom of Spain (ICSID Case No. ARB/97/7), Award of 13 November<br />
2000, para. 64 (“强调双边投资条约并非不良商业判断的保险单”); Marvin Roy Feldman Karpa v. The United<br />
Mexican States (ICSID Case No. ARB(AF)/99/1), Award of 16 December 2002, para. 112 (指出“根据第 1110 条,<br />
并非外国投资者所遭受的所有商业问题都是间接征收或逐渐征收,同样,根据第 1110.1(c)条,也并非都违<br />
反了正当程序或公平与公正待遇”).<br />
31 Cf. FRANCK,见前注 10, p. 675 at p. 678。<br />
32 例见 Elettronica Sicula SpA (ELSI) Cas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Italy), Judgment of 20 July 1989, I.C.J.<br />
Reports 1989, p. 15, para. 74: “显然,不能将(控制和管理)公司的权利解释为是一种使正常的控制和管理<br />
活动永远不会被妨碍的保证。例如,在公共紧急事件或类似事件期间,所有法律制度都必须考虑对正常的<br />
权利行使活动进行干预”。<br />
33 Saluka Investments BV v. The Czech Republic (UNCITRAL), Partial Award of 17 March 2006, para. 302. 另见<br />
Elizabeth SNODGRASS, “Protecting Investors’ Legitimate Expectations”, 21 ICSID Rev. – For. Inv. L. J. 1 (2006,<br />
no. 1) pp. 1-58。<br />
34 See David DYZENHAUS, “The Rule of (Administrative) Law in International Law”, 68 Law & Contemp.<br />
Probs. (2005) p. 127 at p. 133 et seq. 关于澳大利亚与英国的判例法; SCHULZE-FIELITZ (见前注 29), Art. 20<br />
para. 134 et seq. 关于德国宪法; Søren SCHØNBERG, Legitimate Expectations in Administrative Law (2000) on<br />
English, French and EC/EU law; Bruce DYER, “Legitimate Expectations in Procedural Fairness after Lam” in<br />
Matthew GROVES, ed., Law and Government in Australia (2005) p. 184 et seq. 关于澳大利亚法律; 另见<br />
Jean-Marie WOEHRLING, “Le Principe de Confiance Légitime dans la Jurisprudence des Tribunaux” in John W.<br />
BRIDGE, ed., Comparative Law Facing the 21st Century (1998) p. 815 et seq. summarizing a comparative study<br />
by the XV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omparative Law, Bristol/UK in 1998.<br />
35 See Jörg P. MÜLLER, Vertrauensschutz im Völkerrecht (1971). 国外投资者征收法律更为具体的论述见<br />
Rudolf DOLZER, “New Foundations of the Law of Expropriation of Alien Property”, 75 A.J.I.L. (1981) p. 553, at<br />
p. 579 et seq.。<br />
36 Tecmed v. Mexico, 见前注 24, para. 154. 其他一些案件中也采用了该案仲裁庭的做法。参见 ADF v. United<br />
States, Award of 9 January 2003, para. 189; MTD v. Chile, 见前注 27, para. 114 et seq.; OEPC v. Ecuador, 见前
Mexico 案中,仲裁庭解释说“合法期待的概念涉及的是缔约一方的行为使投资者或投资本<br />
身产生了合理和正当的期待,并依赖该行为而行动,例如,NAFTA 缔约方不能兑现这些期<br />
待将使投资者或投资遭受损失。” 37<br />
该理论在范围和适用性上的各种限制还需要进一步检验。一般来说,这种期待可能只有<br />
通过东道国所作出的明示或默示的陈述产生(包括代理、追认和其他与国家有关的机构,他<br />
们同时也受制于有限的规则)。 38 此外,投资者在一般情况下对东道国未来行为的预期并不<br />
能当然地转变为对于特殊情况下东道国行为的“合法期待”,并且在很多情况下,这种预期<br />
应当包含东道国将采取某些监管措施的可能性。国家是承担公共职责的管理者。仲裁庭在<br />
“Eureko v. Poland”案中的意见可能体现了这样的观点,即如果有很好的理由来证明不能满<br />
足投资者期待的原因,那么违反该期待可能并没有违反公平与公正待遇。 39 同样,在“Saluka<br />
v. Czech Republic” 案中,仲裁庭特别提醒过于字面理解投资者期待的危险,因为这将“强<br />
加给东道国不适当和不切实际的义务。” 40 相反,仲裁庭认为如果符合比例原则,那么对于<br />
投资者合法期待的违背是可能的,也是合法的。因为“一方面,违反公平与公正待遇的决定<br />
需要对申请人的合法与合理期待予以权衡,另一方面,也需要对被申请人的合法监管利益予<br />
以权衡”。 41 在此背景下,合法期待的概念需要审慎的比较法分析以及一套完善方法论的应<br />
用。尽管为实现这些目标的理论研究进程已经开始,但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br />
(三)行政正当程序与拒绝司法<br />
正如习惯国际法所一直承认,且许多仲裁庭在适用投资条约时所决定的那样,公平与公<br />
正待遇包含着正当程序要素:具体而言就是指行政和司法正当程序。 42 公平与公正待遇原则<br />
注 22, para. 185; CMS v. Argentina, 见前注 22, para. 279; Eureko B.V. v. Republic of Poland, Partial Award of 19<br />
August 2005, paras. 235, 241.<br />
37 .International Thunderbird Gaming Corporation v.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UNCITRAL/NAFTA), Award of<br />
26 Jan. 2006, para. 147 (内部引文省略).<br />
38 关于期待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关系,参见 ADF v. United States, 见前注 36, para. 189,仲裁庭认为该案没有<br />
违反 NAFTA 第 1105.1 条,在该案中,申请人主张现有的判例法表明一个机构必须给予豁免成文法律规定<br />
的当地成分要求,声称“投资者关于其所引用的判例法的关联性与可适用性的任何期待都不是基于美国联<br />
邦政府的授权机构的误导性陈述而做出的,相反,可能是基于投资者收到的美国私人法律顾问的法律建议<br />
做出的”。<br />
39 See Eureko v. Poland, 见前注 36, paras. 232 et seq.<br />
40 Saluka v. Czech Republic, 见前注 33, para. 304.<br />
41 Saluka v. Czech Republic, 见前注 33, para. 306.<br />
42 迄今为止,在投资仲裁中,国家立法者并没有受制于任何正当程序的概念。但是,正当程序的要求在征<br />
收立法方面是存在的,因为大多数 BITs 明确规定东道国应保证给予受影响的投资者正当程序。See Rudolf<br />
DOLZER and Margrete STEVENS,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1995) p. 106 et seq
因此与民事和刑事司法的适当管理密切联系起来。 43 因此,在“Waste Management v. Mexico”<br />
案中,仲裁庭将违反公平与公正待遇界定为“包括缺乏正当程序导致了违背司法正当性的结<br />
果——例如在司法程序中明显缺乏自然正义或者是在行政程序中完全缺乏透明度和公正性<br />
的情况。” 44 同样,在“ S.D. Myers v. Canada”案中,仲裁庭认为,除其他要素外,公平与公正<br />
待遇还包括“国际法上正当程序的要求。” 45 在“ International Thunderbird Gaming v. Mexico ”<br />
案中,仲裁庭认为一个政府机构的程序“应当经过适用于行政官员的正当程序和程序平等标<br />
准的检验”。 46<br />
有关正当程序的问题也反映在公平与公正待遇同禁止任意性 47 与歧视相联系的判例中。<br />
例如,在“ Loewen v. United States”案中,仲裁庭顺带指出“违反国内法并且歧视外国诉讼当<br />
事人的决定”违反了公平与公正待遇。 48 同样,在“ Waste Management v. Mexico ”案中,仲<br />
裁庭认为“如果武断的、极不公平、不公正或者特殊的、实行差别对待并使申请人受到地区<br />
或种族歧视的行为可归咎于国家,并有害于申请人,那么这类国家行为就违反了公平与公正<br />
待遇。” 49<br />
然而,将国际法标准与规制地法律相结合的正当程序的要求究竟要多明确,这一问题尚<br />
缺乏一个完整的界定,而一些判例中国家违反国内法律的行为,可以作为重要的信息。因此,<br />
在“Metalclad v. Mexico”案中,仲裁庭专注于当地市政府明显滥用建筑法的行为,将其作<br />
为认定违反公平与公正待遇的一个要素。 50 同样,在“Pope & Talbot v. Canada”案中,仲裁庭<br />
认为根据国内法律,某特定机构没有资格针对投资采取行政程序。仲裁庭声称:“在试图迫<br />
使投资符合要求之前,SLD(本案涉及的加拿大某行政机构)应当消除对此问题的任何怀疑<br />
并向投资者告知其行为的法律依据”,而不是依赖“赤裸裸的权力主张和不接受核查即取消、<br />
43 关于国际法上拒绝司法问题更为全面的论述见 Jan PAULSSON, Denial of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Law<br />
(2005)。最近,在美国的条约实践中明确提及将正当程序和拒绝司法的概念作为公平与公正待遇的一部分<br />
。比如,在美国—多米尼亚共和国—中美洲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中的第 10 章第 5.2(a)条规定,“依据世<br />
界主要法律体系中纳入的正当程序原则,公平与公正待遇包括刑事、民事以及行政程序中的不能拒绝司法<br />
的义务”。《多米尼亚共和国、中美洲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签订于 2004 年 8 月 5 日。available at<br />
.<br />
44 Waste Management v. Mexico (ICSID Case No. ARB(AF)/00/3), Award of 30 April 2004, para. 98.<br />
45 .S.D. Myers v. Canada (UNCITRAL/NAFTA), Partial Award of 13 November 2000, para. 134.<br />
46 .International Thunderbird Gaming v. Mexico, 见前注 37, para. 200.<br />
47 尤其可参见 Elettronica Sicula S.p.A. (ELSI) (United States v. Italy), 见前注 32, p. 76, para. 128 (指出“任意<br />
性与其说是违反了某一法律规则,还不如说其违反了法治。在 Asylum 案中,当谈到任意性行动取代了法<br />
治时,仲裁庭也表达了这一观点。这是对法律正当程序的故意漠视,这种行为对司法正当性产生了震动,<br />
甚至带来了冲击”。(内部引文省略))<br />
48 Loewen v. United States, para. 135.<br />
49 Waste Management v. Mexico, 见前注 44, para. 98; similarly Eureko v. Poland, para. 233 (指出国家“并非出<br />
于正当理由,而是出于与歧视性的波兰政治与民族主义的相互作用相关联的完全任意的理由”,因此违反了<br />
公平与公正待遇)。S.D. Myers v. Canada, 见前注 45, para. 266,仲裁庭在该案中也将国民待遇同公平与公正待<br />
遇标准作了区分,其指出:“尽管……仲裁庭认为拒绝给予 NAFTA 中的国民待遇规定并不必然违反最低标<br />
准规定,但多数仲裁庭都认为基于这一特殊事实,违反了 1102 条也必然违反了 1105 条”。<br />
50 Metalclad v. Mexico, 见前注 23, para. 93.
减少或暂停投资分配的威胁”。 51 同样,在“GAMI Investments, Inc. v. Mexico”案中,仲裁<br />
庭从公平与公正待遇中引申出政府不仅应消极遵守此义务,还应积极执行现行的国家法律规<br />
定。 52 在“Tecmed v. Mexico”案中,仲裁庭强调:东道国“在使用法律工具规范投资者行<br />
为和投资时必须与这些工具通常所赋予的职能相符合”。 53<br />
相反,在某些情况下,仲裁庭会将一国行政措施符合有关的国内法律规则作为没有违反<br />
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的依据。例如在“Noble Ventures v. Romania”案中,仲裁庭认定破产程<br />
序“是依法启动和进行的,并没有违反法律”, 54 因此裁定其没有违反公平与公正待遇。同<br />
样,在“ Lauder v. Czech Republic”案中,仲裁庭强调,违反公平与公正待遇通常不包括“监<br />
管机构为执行法律而采取必要的行动”这一情况。 55 这一系列案件大多伴随着对民主的要求,<br />
即公共权力依据法律获得授权并按照预先制定的程序性和实体性规则行使。因此违反国内法<br />
律可能也违反了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平与公正待遇的国际法标准就是一<br />
国法律规定的简单镜像。<br />
(四)透明度<br />
对于外国人和外国投资待遇相关的政府信息和决策程序的透明度,传统习惯国际法的发<br />
展还很不完善。在更广义的国际法上,关于国家政府透明度的国际法律标准的制定和适用一<br />
直是法律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然而,无论是在世界贸易组织,还是产生了《奥胡斯公约》<br />
(Aarhus Convention)这一典范的国际环境法,或者是在国际人权法中,这仍是国际法律实<br />
践中富有挑战性的部分。许多国家,特别是转型期与发展中国家都努力履行在此方面的现有<br />
义务,而且有些国家已经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如智利)或立法,以加快官僚文化的改变与信<br />
息提供的实际进程。此外,确定透明度要求的适当限制,例如隐私利益、商业机密或者国家<br />
安全的保护,是十分复杂的。<br />
因此,对于投资仲裁庭来说,根据并不明确的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继续这一复杂的工作<br />
并不容易,即使一些仲裁庭已经这样做了。因此,在“Metalclad v. Mexico”案中,仲裁庭<br />
认为墨西哥违反了 NAFTA 第 1105 条,因为“墨西哥未能向 Metaclad 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br />
资提供一个透明且可预见的制度”。 56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根据《不列颠哥伦<br />
比亚国际仲裁法》行使管辖权时撤销了这份裁决所涉及的透明度要求。 57 仲裁庭声明:“为<br />
实施、完成并成功地经营投资的目的而作出的所有相关法律规定……应当易于让所有受此影<br />
响的投资者知道”,并且东道国必须“保证能够迅速的确定其正确立场并将之明确表示以使<br />
得投资者确信其行为符合相关的法律,从而能够采取适当的行动”,尽管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r />
51 Pope & Talbot, Inc. v.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UNCITRAL/NAFTA), Award on the Merits of Phase 2 of<br />
10 April 2001, para. 174 et seq.<br />
52 GAMI Investments, Inc. v.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UNCITRAL/NAFTA), Final Award<br />
of 15 November 2004, para. 9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个政府未能执行或者遵守自己的法律并因此<br />
给外国投资者带来不利影响,这有可能但并不是必然就违反了第 1105 条。”<br />
53 Tecmed v. Mexico, 见前注 24, para. 154.<br />
54 Noble Ventures v. Romania, Award of 12 October 2005, para. 178.<br />
55 Lauder v. Czech Republic, 见前注 26, para. 297.<br />
56 Metalclad v. Mexico, 见前注 23, para. 99 (黑体字为作者的强调)。<br />
57 See Supreme Court of British Columbia,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v. Metalclad Corporation, 2001 BCSC<br />
644.
的裁决在某些方面可能有争议,但其对此声明确实是提出了合理的质疑。 58 通过迫使他们重<br />
新调整其优先事项和国家任务,以使其作为权威的咨询机构,甚至是事实上的外商投资项目<br />
实施中的保险人,这种程度的声明确实可能导致行政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得以重新界定。 59<br />
“Tecmed v. Mexico”案中的裁决附带意见也表明了同样的问题,其将合法期待的要素<br />
与推理中的透明度要求在论证中联系起来:<br />
“外国投资者希望东道国的行为前后一致,并且与外国投资者的关系避免模糊并保持<br />
完全透明,使投资者可以事先知道所有将规范其投资的规则和法规以及有关政策和行<br />
政措施或指令的目标,从而能够规划其投资并遵守这些法规。” 60<br />
然而,在“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下,一种对于透明度要求更严格的解读似乎更容易站<br />
得住脚。事实上,在 Tecmed 案中,透明度主要适用于行政法的程序方面,例如给予充分理<br />
由的规定 61 以及以可理解和可预见的方式采取行动的义务。 62 这些框架使外国投资者在行政<br />
程序上的合理地位更加稳固。因此,尽管透明度目前还不是完善的附加性实体要求,但它也<br />
是重要的。此外,它的具体作用十分重要,例如在与举证责任密切联系的程序上有助于解决<br />
国内法律的不确定性。在此方面,比较法方法、详细的分析以及国际法其他领域的规范性标<br />
准的运用非常重要。<br />
(五)合理与比例原则<br />
最后,投资仲裁庭将公平与公正待遇与合理性及比例性的概念联系起来。虽然合理性不<br />
如比例原则在方法上的精确性,但其也可以和比例原则一样用来限制东道国干预外国投资者<br />
被许可的范围。因此,在 Pope & Talbot v. Canada 案中,仲裁庭在认定不存在违反公平与公<br />
正待遇时多次提到了行政机构行为的合理性。 63 合理性的要素还可以被运用到比例检验中,<br />
例如 Tecmed v. Mexico 案的裁决意见指出:“对外国投资者施加的费用和负担应与任何运用<br />
征收措施实现的目标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 64<br />
58 Metalclad v. Mexico, 见前注 23, para. 76 (for both citations)。<br />
59 Stephan SCHILL, “Revisiting a Landmark: Indirect Expropriation and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in the<br />
ICSID Case Tecmed”, 3 TDM (April 2006) p. 15.<br />
60 Tecmed v. Mexico, 见前注 24, para. 154; similarly Maffezini v. Spain, para. 83。<br />
61 See Tecmed v. Mexico, 见前注 24, para. 123 (指出“行政决定必须基于正当的依据以便达到透明度的要求,<br />
从而使不服此决定的个人可以用尽所有法律救济对该决定提出挑战”).。同样可见, Tecmed v. Mexico, para.<br />
164.。<br />
62 见 Tecmed v. Mexico, 见前注 24, para. 160 (指出“关于 INE 与 Cytrar 或 Tecmed 公司之间来往函件中垃<br />
圾填埋场搬迁的附属声明……只要 Cytrar 公司的业务没有搬迁,就不能把该附属声明认为是墨西哥当局改<br />
变其对于许可证范围的立场的意愿的一个明确清楚的表达,也不能将其认为是墨西哥当局对 Cytrar 公司作<br />
出的一个明确、透明、清楚的警告,该警告是拒绝改变撤销 Cytrar 公司将其垃圾填埋场的业务搬迁至另一<br />
个地方的许可证”)。<br />
63 See Pope & Talbot v. Canada, 见前注 51, paras. 123, 125, 128, 155; 另见 MTD v. Chile, 见前注 27, para. 109<br />
以及借鉴了 Schwebel 的专家意见。<br />
64 Tecmed v. Mexico, 见前注 24,para. 122. 关于合理性问题的独立且详细的判例是可以作出的。参见 Olivier<br />
CORTEN, L’utilisation du raisonnable par le juge international: discours juridique, raison et contradictions<br />
(1997)。然而,本文的重点是比例原则,将在第三部分内容中对其予以广泛讨论。
(六)公平与公正待遇要求对国家法律和行政的影响<br />
上述公平与公正待遇的五个要素与政府机构、国家法院和立法机关行使公共权力相关。<br />
它们被用来作为国家政府行为的评价标准,但并非由国内法庭实施。国际条约设立的仲裁庭<br />
用它们作为一国政府行为的评价标准,这是一个典型的行政法职能。尽管上述五个要素在许<br />
多国内法律中也有相应的规定,但“公平与公正待遇”本身在大多数国家的行政法或宪法法<br />
律中并不是一个直接适用的法律标准。然而,在各种扩散与影响进程的作用下,这一国际标<br />
准及其具体组成部分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各国的具体法律和行政行为产生影响。<br />
上述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国际组织,例如世界银行或者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援引投资条<br />
约标准和判例对特定国家的法律和体制改革提供建议的时候。同样,仲裁案件中败诉各国的<br />
政府机构可能会试图影响行政决策的结构和进程。这些进程,以及随着更多的人熟悉仲裁判<br />
例和国际法其他领域在类似问题上的发展而带来的普遍渗透,可能将对国内法下给予外国投<br />
资者或其他主体的程序性权利和补偿,甚至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和审查产生影响。<br />
关于行政程序,特别是对经营许可证的签发,吊销以及续签而言,公平与公正待遇通常<br />
要求国家行政机关给予外国投资者一个陈述案情的公平机会,使他们合理全面地进行诉讼程<br />
序并出具对他们做出决定的理由。例如,在涉及 NAFTA 的 Metalclad v. Mexico 案中,行政<br />
诉讼中公平审理的权利和参与权利起到了作用,仲裁庭以投资者没能充分参与为由认定东道<br />
国违反了公平与公正待遇。仲裁庭认为应当给予投资者参与当地市议会会议的机会,该会议<br />
讨论的是是否对投资者的垃圾填埋场签发建筑许可证。 65 同样,在 Tecmed v. Mexico 案中,<br />
仲裁庭强调在一个关于不予续签垃圾填埋场的经营许可证的行政程序中,听证上的公平是公<br />
平与公正待遇的一部分。仲裁庭还指出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应当对外国投<br />
资者的请求作出决定。 66<br />
公平与公正待遇要求可能促使国家行政机构说明其所作出决定的理由并使其决定立足<br />
于充分的事实证据。这可能潜在的影响了适用 NAFTA 的裁决,例如在 Metalclad v. Mexico<br />
案中,仲裁庭认定墨西哥违反了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因为市议会拒绝签发建筑许可证的决<br />
定并不是基于“建筑方面或物理设施的缺陷”的考虑, 67 其动机主要是出于当地居民对于该<br />
垃圾填埋场的态度。仲裁庭认为,该决定缺乏市政建设法项下合法性标准的相关证据的支持。<br />
提供充分证据的要求还衍生出作出最终决定前应当进行事实调查并核实证据的义务。另外,<br />
要求说明理由的目的在于促进对于一个行政决定的法律审查。 68<br />
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也可能受到公平与公正待遇要求的调整。例如,如果一个国家行政机<br />
关一贯容忍某一特定的非法行为,公平与公正待遇就将对其只针对相同行为的外国投资者的<br />
干预施加限制。 69 同样,投资者的合法期待能够对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设定界限。例如,<br />
65 仲裁庭特别指出“不予续签许可证的决定是在一个市议会上作出的, Metalclad 公司没有接到任何的通知<br />
和邀请,也没有任何机会参加”。参见 Metalclad v. Mexico, 见前注 23, para. 91。<br />
66 See Tecmed v. Mexico, 见前注 24, para. 161 et seq. 关于公平与公正待遇下听证公平要素的详细论述,见<br />
Todd G. WEILER, “NAFTA Article 1105 and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42 Columbia J.<br />
Transnat’l L. (2003) p. 35 at p. 79 et seq.。<br />
67 Metalclad v. Mexico, 见前注 23,para. 93。<br />
68 See Tecmed v. Mexico, 见前注 24, para. 123。<br />
69 Cf. Steffen HINDELANG, “‘No Equals in Wrong?’ The Issue of Equality in a State of Illegality – Some<br />
Thoughts to Encourage Discussion”, 7 J. World Inv. & Trade (2006) p. 883.
实施与政府官员作出的陈述相反的行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构成违反了公平与公正待遇。 70<br />
上述的一些要求对于国家的司法实践也有影响。例如,在 Mondev v. United States 案中,<br />
仲裁庭认可这样一种情况:“若某公共权力的行为影响了基于 NAFTA 的投资,则对该行为<br />
的诉讼一概予以豁免就等于违反了 NAFTA 第 1105.1 条”。 71 在 Azinian v. Mexico 案中,仲裁<br />
庭指出“如果有关法院拒绝受理诉讼案件,或使之受到不必要的延误,或以一种极不恰当的<br />
方式行使审判权,则可以对这一拒绝司法行为提起申诉”。 72 外国投资者能够诉诸于国内法<br />
院也是一个要求,其为确保司法参与权的义务在国际上的广泛争论提供了一个开端。一般来<br />
说,法院必须及时受理诉讼案件,在所有重要问题上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一个公平的庭审程序,<br />
并且用理由充分的法律依据作出判决。 73 司法程序的标准与那些人权公约(如《欧洲人权公<br />
约》第 6 条)确立的标准大致相同。 74 但是,行政程序受到的特殊影响可能会更显著。<br />
总之,公平与公正待遇要求国内行政程序如同司法程序一样,应当符合从合法性和良性<br />
治理的程序导向性观念中得出的标准。 75 目前极不明确的是这种发展中的投资条约理论,以<br />
及与其同时发展的一系列全球行政规则,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对国家实践产生影响。不过显<br />
而易见的是,如同仲裁庭近年来所解释的那样,目前非常多的条约都包含“公平与公正待遇”<br />
标准,其应该(站在政府律师意见的角度)会影响国家在投资成立后对其自身监管框架的任<br />
何变化的考虑, 76 并且更应当促使国家使其国内法律秩序与那些符合法治概念且被国际所公<br />
认的标准相适应。<br />
虽然在关于良好行政和外国投资者的待遇方面,一些专家指导和改革的推力来自于世界<br />
银行和与贫困或转型国家有关的类似机构,但仍然缺少像人权机构、欧盟或世界贸易组织这<br />
类完善的国际组织性动力来推动事前的改革。虽然事后仲裁的损失风险似乎并不容易辐射到<br />
事前的行政改革, 77 但也有一些明显的例外。中国学者指出,外国投资者可能会考虑对中国<br />
70 See International Thunderbird Gaming v. Mexico, 见前注 37, para. 137 et seq.; Metalclad v. Mexico, para. 85<br />
et seq.。<br />
71 See Mondev v. United States (ICSID Case No. ARB(AF)/99/2 (NAFTA)), Award of 11 October 2002, para. 151<br />
(然而,仲裁庭认为本案中给予市政当局的豁免权,并没有违反公平与公正待遇)。<br />
72 Robert Azinian, Kenneth Davitian, & Ellen Baca v.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ICSID Case No. ARB<br />
(AF)/97/2 (NAFTA)), Award of 1 November 1999, para. 102.<br />
73 See Azinian,同上,para. 102。<br />
74 .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and its protocols, 4<br />
November 1950, 213 U.N.T.S. 222. 关于此类推论见 Mondev v. United States, 见前注 71, para. 144。 另见<br />
Andrea BJORKLUND, “Reconciling State Sovereignty and Investor Protection in Denial of Justice Claims”, 45<br />
Va. J. Int’l L. (2005) p. 809。<br />
75 关于欧盟/欧共体中跨国行政法在行政程序方面的相似发展,以及跨国行政法在 WTO 法律中的相似发展,<br />
参见 Giacinto DELLA CANANEA, “Beyond the State: the Europea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Procedural<br />
Administrative Law”, 9 Eur. Publ. L. (2003) p. 563.<br />
76 关于此问题见 Rudolf DOLZER,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A Key Standard in Investment Treaties”, 39<br />
Int’l Law (2005) p. 87 at p. 100 et seq.<br />
77 Cf. Tom GINSBURG, “International Substitutes for Domestic Institutions”, 25 Int’l Rev. L. & Econ. (2005) p.<br />
107; Susan D. FRANCK,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19<br />
McGeorge Global Bus. & Dev. L. J. (2007) p. 337.
提起仲裁程序,这能产生有益的改革效果。 78 纳米比亚的一个法院在涉及到纳米比亚与德国<br />
的 BIT 的案件中,基于不适当的磋商和其他程序性理由,认为政府计划对缺席方的德有农<br />
场采取的征收措施违法。对此问题进行的系统研究是必要的,其有可能影响国家实践和政策。<br />
无论如何,仲裁庭作出的公开和深入分析的判决对之后的政府治理有所影响;这一现实也使<br />
得仲裁员有责任将判决建立在对案件问题的深入了解和具体问题的细致分析之上。<br />
(七)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在适用方法上的改革<br />
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的模糊性使得仲裁庭在对其进行解释和说明时遇到了重要问题。由<br />
于涉及国家行政行为的原则在其职能上缺乏任何成熟的概念,仲裁裁决只能在曲折中发展。<br />
因此仲裁裁决的推理在法律分析方面经常很薄弱,有时甚至无法令人信服。仲裁庭自身经常<br />
局限于援引同样无说服力的先例或者以一种不确定的方式来阐述 BITs 的目的和宗旨,而对<br />
于这些具体的解释是如何基于国际法上完善的条约解释方法作出的,裁决中没有任何更深入<br />
的理由。最终,这些缺陷将危及到公平与公正待遇的适当性,使其成为与东道国行为的可预<br />
见性相冲突的概念。<br />
此外,判例还产生了一些使受害国不能普遍接受且几乎肯定不会被国内适用程序所采纳<br />
的结果和附带意见,而对于东道国的行为有宽泛溯及力的“只要我看到,我就知道”( I will<br />
know it when I see it)式的监管,一些裁决不仅认同而且可能加以赞赏。 79 然而,可预见性的<br />
适用对东道国和外国投资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都需要事先知道何种措施将引起国家的<br />
国际责任,并且相应地,还需要事先知道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对何种政治和行政风险予以保<br />
护,以及与此相反,何种风险由投资者承担或应单独投保。<br />
要具体说明“公平与公正待遇”对政府行政机构的实际要求是什么,就需要一种解释与<br />
适用“公平与公正待遇”条款的方法,该方法要比仲裁庭通常采用的方法更为全面。与其依<br />
赖于对先前仲裁裁决的一连串抽象引用(一种几乎没有用处的做法,尤其是当争端涉及新的<br />
情况时)或以抽象的方式假定公平与公正待遇的内容却没有充分的正当理由,仲裁庭更应当<br />
运用一种对国内和国际法在良好行政上都有借鉴的比较方法,并以此作为国际条约法和法律<br />
决策的解释学的一部分。仲裁庭因此应当对主要的国内法律制度以及国际法律和国际组织中<br />
的主要方法进行一个比较分析,以便掌握这些规定公共权力行使的法律制度的共同特征。<br />
这种对于国内法的比较分析可能至少在两个方面对仲裁庭的判例产生影响。第一,它可<br />
能使投资仲裁庭积极地从公平与公正待遇具体情形解释的国内法治标准中推断出机构性和<br />
程序性要求。例如,对国内法律制度以及他们的法治概念的比较分析可以用来证明外国投资<br />
者必须履行的行政程序标准的正当性。 80 第二,对国内法项下的法治含义的比较分析可以为<br />
国家根据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针对外国投资者的行为提供正当理由。如果类似的行为由于符<br />
合他们对于国家法治的理解而被国内法律制度普遍接受,例如在紧急情况下国家下令修改私<br />
人抵押借款合同中取消抵押物赎回权的规定,那么投资仲裁庭可将这类裁决作为对一般法律<br />
原则的表述,转换到国际投资条约的层面上来。<br />
78 Xiuli HA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in Tecmed v. Mexico”, 6 Chinese J. Int’l L.<br />
(2007) p. 635, 指出了这样的迹象,主要是关于间接征收。<br />
79 对间接征收概念的背景比较,见 Yves FORTIER and Stephen L. DRYMER, “Indirect Expropriation in the<br />
Law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 Know It When I See It, or Caveat Investor”, 19 ICSID Rev. – For. Inv. L. J.<br />
(2004) p. 293。<br />
80 See della CANANEA,见前注 75, p. 563 at p. 575 (解释道,为了对 WTO 成员国行使公共权力时对其施加<br />
法律要素的程序规则,WTO 上诉机构在 Shrimp-Turtle 案中已采纳国内法律秩序的一些一般或‘全球性’<br />
的行政法原则)。
然而,分析不应当仅限于国内的法律制度,那些与其他国际法律制度的交叉比较,也越<br />
来越富有成效。前面已经提到了欧洲人权法院关于《欧洲人权公约》第 6 条的判例,而欧洲<br />
行政法的新兴原则现在也是很多学术和政策研究的主题。 81 对于公共权力行使的有关要求来<br />
说,WTO 上诉机构的判例也是一个重要来源。例如,在虾龟案的第一项裁决中,上诉机构<br />
认为来自印度、泰国和其他国家的虾被不正当的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美国在适用其海龟保<br />
护立法时所遵循的行政程序构成了“成员国之间武断的和不合理的歧视”,因此,美国的海<br />
龟保护措施不能被认为是 GATT 第 20 条中的例外。上诉机构指出,美国对特定国家虾产业<br />
是否符合其海龟保护标准所采取的检验程序:<br />
“—没有给申请国一个听证或对自身不利的任何意见做出回应的正式机会...<br />
—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都没有给出正式书面的、合理的决定...<br />
—没有该决定的通知,并且<br />
—没有对驳回决定的审查或上诉程序”。<br />
比较分析包括发现差异和相似之处。国际投资条约具有显著的实质性特点,在条约项下,<br />
仲裁庭的机构性特点和作用也十分显著。然而,保护和促进外国投资并不是机制本身的目的。<br />
它们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目标是密切相关的,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被明确规定为《解决<br />
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ICSID 公约》) 的目标,即承认“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br />
进行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以及国际私人投资在其中的作用”。 82 作为一个发展机构,世界银<br />
行进一步加强了外资流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 83 根据《ICSID 公约》,国际投资争端解决<br />
机制实施的目的在于减少与投资有关的政治风险,即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机构较弱并且法<br />
律和政治基础极其不稳,以及其自身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利益而给外国投资带来的政治性风<br />
险。 84 该体制目前的运作是否已实际上达到了这些目标,现在新的和更复杂的目标和限制是<br />
否是个别条约或整个体制目的的一部分,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考虑因素。充分考虑所有相关<br />
因素进而做出判例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这至少应在观念上将其与国际投资仲裁制度的基本规<br />
范性依据联系起来。本文第五部分将对这些基本规范性理由予以讨论。本文接下来研究仲裁<br />
81 例见 Paul CRAIG, EU Administrative Law (2006); Carol HARLOW, Accountability in the European Union<br />
(2003); Francesca BIGNAMI and Sabino CASSESE, eds., “The Administrative Law of the European Union”, 68,<br />
Law & Contemp. Probs. (2004) p. 1; Sabino CASSESE, ed., Trattato di Diritto Amministrativo, 2nd edn. (2003);<br />
Jürgen SCHWARZE, Europäisches Verwaltungsrecht, 2nd edn. (2005)。<br />
82 参见《ICSID 公约》序言。<br />
83 Aron BROCHES, The 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br />
Other States, 136 Recueil des Cours (1972-II) p. 331 at p. 342 et seq.; Burkhard SCHÖBENER and Lars<br />
MARKERT, “Das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ICSID)”, 105 ZVglRWiss (2006) p.<br />
65 at p. 67.<br />
84 关于机构与经济增长之间联系的讨论,参见: Edgardo BUSCAGLIA, William RATCLIFF and Robert<br />
COOTER,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1997); Jean-Philippe PLATTEAU, Institutions, Social<br />
Norm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2000); Dani RODRIK, Arvind SUBRAMANIAN and Francesco TREBBI,<br />
“Institutions Rule: The Primacy of Institutions Over Geography and Integr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9 J.<br />
Econ. Growth (2004) p. 131; 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ROBINSON, “Institutions as the<br />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 in Philippe AGHION and Stephen DURLAUF, eds., Handbook of<br />
Economic Growth (2005). For a sceptical view on causality betwee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see<br />
Edward L. GLAESER,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 “Do<br />
Institutions Cause Growth?”, 9 J. Econ. Growth (2004) p. 271。
庭基于审查国家行为的治理任务而作出的实际行为的问题,特别是对法院和仲裁庭行使审查<br />
职能时所确立的治理方法(例如比例分析)的比较研究。<br />
三、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中的比例原则:仲裁庭作为东道国行使监管权力的审查<br />
机构<br />
人们质疑投资仲裁庭对国家行使权力,通常包括对投资者权利条款在用语上太过开放的<br />
批评。人们也会对仲裁庭削弱了国家作为保护公共利益的监管者的作用予以关注,而不论这<br />
些监管是出于环境保护、人权或应对紧急事件,还是仅仅为了保护财产权利和经济利益,这<br />
在国家通过抽象和一般规定履行监管者职能时尤其如此。因为投资条约只对与投资者和投资<br />
有关的国家义务予以框架性规定,却并没有制定清晰的文本标准规定如何限制或背离此义务<br />
以符合其他重要利益的公共监管目的,投资条约仲裁庭因此日益意识到运用比例原则进行分<br />
析的必要,本部分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br />
在不同的原则和合法公共目的相互抵触和冲突的情形下,比例分析是一种法律解释和决<br />
策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其并非以“全有或全无的方式”为区分原则,而是允许一种“或<br />
多或少”的模式。 85 法律规则“在事实和法律框架内有着固定的点”,即法律规则是一种“符<br />
合或不符合”的模式。 86 与之相反,法律原则在实践中的不同点在于其目标是“要求在事实<br />
和法律可能的范围内最大程度地实现某事”。 87 正如倡导比例原则的德国著名学者所指出的:<br />
“规则之间的冲突是在有效性层面发生的”,而“原则之间的冲突是在重要性方面发生的。”<br />
88 相比之下,尽管欧洲一体化进程对英美法系的方法有影响,但美国的法官们以及那些历史<br />
上受过英国影响的法律体系对比例分析的热情已有所减退。 89<br />
除了要面对重大的问题,支持运用比例原则的理由也是很充分的。比例分析有助于投资<br />
保护标准概念的适用,当国家的监管空间留有余地时,比例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融入到<br />
间接征收及公平与公正待遇的概念中。 90 比例原则由此来平衡外国投资者的利益、一般的财<br />
产权利以及相互冲突的公共利益。比例分析容易成为为特定司法价值正名的方法,但当先进<br />
的法院和仲裁庭在国内和国际案件中运用比例分析来应对开放性概念与困难的平衡时,其比<br />
85 Ronald DWORKIN, Takings Rights Seriously (1978) p. 24.<br />
86 Robert ALEXY,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1986; transl. Julian Rivers, OUP 2002) pp. 47-48.<br />
87 Robert ALEXY, On the Structure of Legal Principles, 13 Ratio Juris (2000) p. 294 at p. 295. 另见 ALEXY,<br />
见前注 86, p. 47, 指出原则是“鉴于法律与事实的可能性,要求最大程度地实现某事”的规范。<br />
88 ALEXY,同上,p. 50。<br />
89 关于美国宪法中,特别是刑法第八次修正案中比例性要求的范围,参见 Alice RISTROPH, “Proportionality<br />
as a Principle of Limited Government”, 55 Duke L. J. (2005) p. 263 with further references; see also on the<br />
hesitance in US constitutional law to accept proportionality as a general principle Vicki C. JACKSON,<br />
“Ambivalent Resistance an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ism: Opening up the Conversation on ‘Proportionality’,<br />
Rights And Federalism”, 1 U. Pa. J. Const. L. (1999) p. 583。<br />
90 这限制了比例分析作为一个法律工具的范围和适用。因此,国家作为国际投资合同的当事人的情况通常<br />
不会被包括在内。关于国家权力在作为国际投资合同当事人能力的限制,参见 Stephan SCHILL, “Enabling<br />
Private Ordering – Function, Scope and Effect of Umbrella Claus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ies”, 18 Minn.<br />
J. Int’l L. (2009) p. 1. 此外,关于财产利益与非财产利益的冲突,已有明确的优先决定控制规则,在此情况<br />
下,通常并不遵循比例推理和分析。而当国家为了保护某些非经济利益而采取一般立法或行政管理手段对<br />
财产权利实施再分配或者干预时,会更多的适用比例分析。
“公平与公正待遇”条款或者间接征收概念中适用的各种推理方法更为可行且更为连贯和普<br />
遍。比例分析方法的广泛运用说明对不同的国内法制度、跨国及国际仲裁庭进行广泛且有启<br />
发的比较法研究和分析(即比例性)是可能的。<br />
此外,与目前的判例相比,比例原则可能在某些方面为国际投资争端中的决定提供了一<br />
个更严格的制度。它要求仲裁员对相抵触的法律诉求予以估量、权衡及考虑替代方法等,并<br />
且为其裁决提供合理的理由。当然,人们也可能批评比例分析为法官造法提供了正当理由并<br />
由此产生了“法官型政府”。但是与目前国际投资法中使用的一些应对价值取舍难题的替代<br />
方法相比,比例分析方法更为完善。如果没有比例分析,间接征收概念将面临如“只要我看<br />
到,我就知道”式的缺乏合理性分析的危险。 91 同样,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的一些子领域会<br />
对仲裁员的主观评价(一个衡平的标准,而不是具有规范内容的法律标准)敞开大门,以此<br />
来替代法治标准下对投资者的期待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所采取的结构性分析和平衡。就此<br />
而言,比例原则能比那些难懂的权衡标准提供更大的可预见性,这在强调比例原则的程序或<br />
形式方面(而非某些国内法院采取的更为实质性的形式)时尤其如此。<br />
在投资条约仲裁中,比例分析和类似的平衡方法在适用上的基本问题是比例分析与准据<br />
法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所适用的国际法之间的关系。 92 该问题的起点是对适用的条约进行<br />
善意的解释。大多数投资条约的突出特点是,它们对于投资者的权利作出的规定并没有全面<br />
地处理这些权利与国家持续的监管权力之间的关系。缔约国通常并不希望这些监管权力受到<br />
严重阻碍,通过参照上下文并按照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善意地理解适用的条约文本,就会发现<br />
对条约的解释需要在投资者保护与国家监管权力之间取得一个平衡。为了使条约解释能够适<br />
用于具体争端,解释者可能也需要依赖缔约方之间所适用的其他相关国际法律规则(如《维<br />
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3(c)条,以及一般的法律原则。通过这种方式,比例原则的适用<br />
能够符合对投资条约的实质条款的解释与适用,并成为其形式之一。<br />
投资条约仲裁庭(至少默示的)对投资条约的制度性规定也予以解释和适用,这些规定<br />
主要是仲裁庭设立和运作的依据。就像本文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提到的那样,这些规定不仅<br />
包括仲裁庭的制度设计与工作范围,还为仲裁庭工作中不可回避的治理职能提供了基础。这<br />
些条约规定的文本与仲裁庭治理作用的关系通常比较松散,并且对它的解释也需要考虑上下<br />
文、目的、宗旨以及其他有关材料。这也包括涉及司法决策机构的作用和职责的一般法律原<br />
则,以及涉及仲裁庭程序适当问题的全球行政法原则,但是涵盖范围较广的法律原则,例如<br />
比例原则,也可能有助于这些仲裁庭在其组织条约项下评价国家行为时落实其合理的作用和<br />
功能。对于仲裁庭的解释功能(即文本解释)与治理功能间的关系,还有一些复杂的问题本<br />
文没有进行详细论述。此处的重点是在仲裁程序中必须全面和公平的权衡投资者保护与其他<br />
合法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因为缔约国加入某一特定的国际投资条约并不意味着其需要舍弃<br />
其他的公共利益。因此,比例分析为平衡不同利益提供了一个理性的程序,这本身也是对投<br />
资条约的合理解释。 93 在此背景下,本部分简要介绍了比例分析在国内与国际仲裁和争端解<br />
决中的发展与传播情况,分析了其方法论结构,并研究了仲裁庭在一些具体国际投资争端中<br />
对这种推理方法的运用。<br />
(一)比例分析的发展与传播<br />
91 FORTIER and DRYMER, 见前注 79, p. 293。<br />
92 在仲裁庭分析或适用国内法律时,可能直接涉及对国内法某一特定领域适用比例分析或者其他平衡方<br />
法,但这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br />
93 See MTD v. Chile, 见前注 27, para. 113; Saluka v. Czech Republic, 见前注 33, para. 297。
本部分对于国内与国际司法机构针对侵犯其他权利的国家行为而运用比例分析的情况<br />
作了一个基本的说明,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反映出可能存在的一般性原则。不同的机构设置<br />
以及不同的条约文本之间的区别是非常大的,所以人们不能将细节分析和背景假设从一个国<br />
际条约机构照搬到另一个,对这一点的强调非常重要。<br />
在国内法渊源方面,比例原则源自于界定国家与其公民之间关系的方法。该方法一方面<br />
有助于解决个人权利与国家利益的冲突,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解决个人利益间的相互冲突。比<br />
例原则“在公共权力干预公民私人领域这一问题上施加了重要的限制” 94 ,并且“提供了一<br />
种界定与限制政府监管自由的工具。 95 它有助于界定和平衡“公共”和“私人”间的关系,<br />
前者以国家或相关社会团体的根本利益和施行的干预为代表,后者以相关的个人利益为代<br />
表。<br />
比例平衡是从德国行政法和宪法中诞生的一个概念,作为一种平衡权利和利益冲突的方<br />
式,其随后被引入南美洲、中欧、东欧以及许多普通法国家。 96 德国宪法法院(德国联邦宪<br />
法法院)创造性地在 Apothekenurteil 案中第一次对比例检验进行了阐述,该案中政府通过限<br />
制医药许可证的数量以保障药品的供应,该许可证制度干预到了药剂师的职业自由。在解决<br />
潜在的权利冲突时,德国宪法法院指出,个人权利与法律的公共目的必须予以平衡:<br />
“宪法权利的目的应该是保护个人的自由,而监管的目的应该是确保对社会利益的充分<br />
保护。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越是受到阻碍,个人因主张自由而产生的影响就会越大;而<br />
自由执业带来的缺陷越多,对公众意愿的保护就越发紧迫。当试图以最有效的方法最大<br />
限度的满足这两个需求时,解决的方法只能取决于审慎的权衡(Abwägung)这两个相对<br />
甚至是相冲突的利益。” 97<br />
加拿大最高法院在 Regina v. Oakes 案中也适用了一个非常类似的比例性检验。该案涉及<br />
《毒品法》中的一项规定是否与《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相符合,前者确立了一个有争议<br />
的推论,即只要发现一个人持有毒品即确定其正在贩卖并要因此承担刑事责任。最高法院以<br />
其违反了宪章中的无罪推定为由推翻了该规定,法院的分析基于一个三步式的“比例检验”:<br />
“第一,所采取的措施必须经过仔细的设计以实现有关目标。它们不能是武断的,不公<br />
平的,也不能基于不合理的考虑。总之,它们必须与目标合理的联系起来。第二,即使<br />
运用的方法在第一层意义上已与目标合理地联系,也应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对有关权利或<br />
自由的损害。第三,限制宪章权利和自由的措施产生的效力必须和‘十分重要’的目标<br />
之间存在合理的比例关系。” 98<br />
南非宪法法院在平衡个人权利与政府目的时也运用了比例性检验。在 State v.<br />
94 Jürgen SCHWARZE,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Impartiality in European<br />
Administrative Law”, 1 Rivista Trimestrale di Diritto Pubblico (2003) p. 53.<br />
95 Mads ANDENAS and Stefan ZLEPTNIG, “Proportionality: WTO Law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42 Tex.<br />
Int’l L. J. (2007) p. 371 at p. 383.<br />
96 See on this and the following Alec STONE SWEET and Jud MATHEWS, Proportionality Balancing and<br />
Global Constitutionalism, Yale Law School Faculty Scholarship Series No. 14 (2008). 此文也发表在 47<br />
Columbia J. Transnat’l L. (2008) p. 72, 但本文中引用的是耶鲁版的页码。<br />
97 BVerfGE 7, 377, 404-405.<br />
98 R. v. Oakes, [1986] 1 S.C.R. 103, 139.
Makwanyane 案中,法院面临对死刑制度提出的挑战,其认为死刑侵犯了反对残忍、不人道<br />
及有辱人格的惩罚的宪法权利。根据宪法法院院长 Chaskalson 的主导意见,法院决定以比<br />
例分析为基础解决此冲突:“在一个民主社会,为了合理与必要的目的而限制宪法性权利涉<br />
及到对相抵触价值的权衡并最终进行比例上的评价。” 99 法院认为需要考虑下列因素:<br />
“在权衡的过程中,有关的考虑因素包括受限制权利的性质以及该权利对于一个以自由<br />
和平等为基础的开放民主社会的重要性;限制该权利的目的以及该目的对于社会的重要<br />
性;权利限制的范围与效力,尤其是在何处施加限制是必要的,其目标能否通过损害较<br />
小的其他手段得以合理实现。” 100<br />
作为一种划分和平衡国际法律秩序与国内公共政策的利益冲突的方法,比例原则也经常<br />
被应用于国际法律制度中。例如,在欧共体/欧盟范围内,欧洲法院(ECJ)曾使用比例原则<br />
来平衡欧共体的基本自由(货物、服务、劳动力及资本的自由流动)与成员国之间互相冲突<br />
的合法利益。 101 在 Cassis de Dijon 案中,欧洲法院判决认为,《欧共体条约》第 28 条保护<br />
的货物自由的流动,不仅可能被一个成员国的歧视性规定侵犯,还有可能受到那些限制了共<br />
同体内部贸易的非歧视性规则的侵犯。然而,出于对基本自由理解的推论,法院同时承认:<br />
如果该公共利益构成一项“强制性规定”,成员国可以据此限制货物的自由流动。法院认为:<br />
“对于有关产品销售的国内法律的差异所造成的共同体内部流动障碍,在其范围内是应<br />
当予以接受的,因为这些不同的规定可能是为了符合强制性规定,尤其是那些关于财<br />
政监督的有效性、公众健康的保护、商业交易的公平以及消费者保护的规定”。 102<br />
尽管法院将上述检验作为一个必要措施,该措施着眼于那些限制较少的替代方法,但该<br />
措施与前述有关国内法院所采用的比例性检验非常类似。<br />
同样,欧洲法院和欧盟初审法院要求应当运用比例原则的标准来评价欧共体针对成员国<br />
采取的措施以及那些欧共体法律秩序下影响到个人的措施。例如,初审法院在一个关于审查<br />
共同体行为的案件中解释道:<br />
“作为欧共体的基本法律原则之一,比例原则要求欧共体机构所采取的措施在追求相关<br />
立法设立的合法目标时,不得超过合理和必要的范围,而且当同时存在几个适当的措施<br />
时,必须选择代价最小的那个,造成的损害也不得超过前述目标的比例”。 103<br />
在欧洲法院的判例中,比例原则既被用来“协调权利与自由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关系,也<br />
99 State v Makwanyane & Another, 1995 (3) SA 391, 436 (CC).<br />
100 同上。<br />
101 另见 Evelyn ELLIS, ed.,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in the Laws of Europe (1999); on proportionality as a<br />
principle in EU/EC law Nicholas EMILIOU,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in European Law: A Comparative<br />
Study (1996) p. 23 et seq.; Georg NOLTE, “General Principles of German and European Administrative Law – A<br />
Comparison in Historic Perspective”, 191 Mod. L. Rev. (1994) p. 191; see also T. Jeremy GUNN, “Deconstructing<br />
Proportionality in Limitations Analysis”, 19 Emory Int’l L. Rev. (2005) p. 465。<br />
102 Cassis de Dijon, ECJ 120/78, Judgment of 20 Feb., 1979 – 见 [1979] ECR 649, para. 8。<br />
103 Case T-13/99, Judgment of 23 November 2002 – Pfizer Animal Health SA v. Commission, [2002] ECR II-3305,<br />
para. 411 (citing [1990] ECR I-4023, para. 13).
用于协调欧共体/欧盟与其成员国之间的权力关系”。 104 因此,它不仅是个人权利和国家对个<br />
人权利的限制权之间的界定方法,也是“超国家的法律秩序与国家法律秩序之间的协调机<br />
制”。 105<br />
在国际公法的其他领域,比例原则在解决平等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关系时也起着类似的<br />
作用。在反制措施法中,人们用比例原则来限制一国对另一国违反国际法时所采取的反制措<br />
施。 106 在此,比例原则对该反制措施的方式和范围施加了限制。 107 反制国尤其不能以永久剥<br />
夺 违法国 平 等 享 有 的 利 益 为 目 的 来 设 计 反 制 措 施 。 正 如 国 际 法 院 ( ICJ )在<br />
Gabcíkovo-Nagymaros 案中所指出的:“一项反制措施的效果必须与遭受的损害相称,并对<br />
有关的权利加以考虑”。 108 同样,在自卫权理论中,比例原则是使用武力的合法要素之一。<br />
尽管《联合国宪章》第 51 条对其没有明确体现,但国际法院认为其已构成习惯国际法的一<br />
部分,因为“自卫只有在所采措施和遭受的武装攻击成比例,并且是出于必要时才是正当<br />
的”。 109<br />
在 WTO 法律制度下,比例分析在平衡国际贸易制度的目标(尤其是贸易自由化,贸易<br />
方面的非歧视以及对非关税贸易壁垒的限制和审慎评价)与相冲突的政府合理目标(诸如对<br />
公共健康,公共道德与环境的保护等大多列举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20 条中的目标)<br />
时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尽管研究世界贸易组织的学者坚持认为在争端解决机构平衡贸易<br />
与非贸易利益的判例中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比例分析原则, 110 但这些不同的平衡方法在抽象的<br />
层面上仍然可以算作是比例分析的一种形式。<br />
在 Korea Beef 案中,为了保障公众健康,韩国政府根据牛肉是否源自韩国而贴上不同<br />
标签并据此销售。上诉机构指出:<br />
“一项执行措施的接受程度与涉及的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的重要程度是正相关的。在评<br />
价该措施是否必要时,需要考虑该措施的其他方面。其一是该措施在多大程度上有助<br />
于所追求目标的实现,以及如何确保对相关法律或规则的遵守。其帮助越大,就越容<br />
易被认为是‘必要的’ ……然而,判断一种可选择的措施在第 20 条(d)项下是否‘必<br />
要’,需要在每个案件中都有一个对一系列因素予以权衡的过程,这些因素主要包括该<br />
措施对于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的作用,受这些法律法规保护的公共利益和价值的重要性,<br />
104 STONE SWEET and MATHEWS, 见前注 96, p. 48。<br />
105 同上。<br />
106 Thomas M. FRANCK, “On Proportionality of Countermeasures in International Law”, 102 A.J.I.L. (2008) p.<br />
715.<br />
107 Enzo CANNIZZARO, “The Role of Proportionality in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Countermeasures”, 12 Eur. J.<br />
Int’l L. (2001) p. 889, at p. 897.<br />
108 Gabcíkovo-Nagymaros Project (Hungary/Slovakia), Judgment of 25 September 1997, I.C.J. Reports 1997, p. 7,<br />
para. 85.<br />
109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 Judgment of 27 June 1986, I.C.J. Reports 1986,<br />
p. 14, paras. 176, 194; 另见 Legality of the Threat or Use of Nuclear Weapons, Advisory Opinion of 8 July 1996,<br />
I.C.J. Reports 1996, p. 226, paras. 41-42 (此处直接指出“在必要和比例的条件下行使自卫权是一项习惯国际<br />
法规则”)。<br />
110 See Axel DESMEDT, “Proportionality in WTO Law”, 4 J. Int’l Econ. L. (2001) p. 441.
以及法律法规对进出口造成的附带影响。” 111<br />
最后,比例原则在欧洲人权法院就《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作出的判例中起着<br />
关键作用,这尤其表现在处理公约赋予的个人权利与成员国的公共政策间的冲突的判例中。<br />
例如,尽管公约在言论自由的限制问题上规定一国的措施必须符合“在民主社会所必须的”<br />
这一条件,但是法院将该条件发展成和德国宪法中类似的比例分析原则。在著名的 Handyside<br />
v. the United Kingdom 案(涉及因违反公共道德而对某书籍进行审查)中,法院认为在第十<br />
章第二段中“‘必要的’一词,并不等同于‘必不可少的’,它也没有‘可接受的’……‘有用<br />
的’,‘合理的’或‘可取的’这类词语的弹性”。 112 随后,在 Dudgeon v. the United Kingdom<br />
案中,法院认定将特定同性恋行为列为犯罪的国家措施是“有失比例的”,因为其对隐私权<br />
造成了干涉。 113 同时,法院对于公约所规定的几乎每一种权利都进行了比例式的平衡。 114<br />
然而,正如在 Handyside 案中所表明的一样,法院允许成员国“在对‘必要性’包含的<br />
迫切社会需求进行初步评估时”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115 国家首先决定什么是一个民<br />
主社会所必要的措施,欧洲人权法院则对这种选择进行审查。裁量权的空间因所涉权利、政<br />
府目标以及干预程度的不同而变化。与欧共体/欧盟对待比例原则的态度相似,斯特拉斯堡<br />
法院认为比例分析不仅平衡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而且还是欧洲人权法院与国内法律制度及<br />
各种国家制度间的一个基本协调机制。 116<br />
(二)比例分析的结构<br />
比例原则意味着在特定政府行为的目标与为达此目标所采取的手段之间是一种手段与<br />
目的关系。 117 当然,比例分析的不同形式和方法之间存在重大区别,例如在全面的比例分析<br />
和程序性的比例分析之间就是如此,前者建立在审查者对影响平衡的政治决策所做的实质性<br />
审查上,后者则基于对诸如较小或最小限制措施等方面所做的检验。 118 相冲突的权利与利益<br />
之间的平衡取决于社会文化、特定机构的价值取向、解释学、核心法律文件、其他的法律材<br />
料以及特定法律制度的目的。尽管存在这些差异,比例分析仍在整体上为决策者提供了一个<br />
指导,其要求决策者处理特定问题并且确定国家采取措施时是否对所干预的权利和利益进行<br />
了充分考虑。许多国内与国际法院在判例中的发展表明,比例原则应当包含三个元素:(1)<br />
适当性原则,(2)必要性原则,(3)狭义上的比例原则。<br />
1 政府合法目的的适当性<br />
比例原则的第一步是分析国家或政府机构采取的措施是否服务于政府的合法目的以及<br />
111 Appellate Body Report, Korea – Measures Affecting Imports of Fresh, Chilled and Frozen Beef, para. 164,<br />
WT/DS161/AB/R (11 December 2000).<br />
112 Handyside v. United Kingdom, App. No. 5493/72 (Eur. Ct. H.R. December 7, 1976), para. 48.<br />
113 Dudgeon v. United Kingdom, App. No. 7525/76 (Eur. Ct. H.R. 22 October 1981).<br />
114 Julian RIVERS, “Proportionality and Variable Intensity of Review”, 65 Cambridge L. J. (2006) p. 174, at p.<br />
182.它尤其对英国法院适用的更为宽松的合理性标准进行了严厉批判,见 STONE SWEET and MATHEWS,<br />
见前注 96, pp. 51-53。<br />
115 同上。<br />
116 STONE SWEET and MATHEWS, 见前注 96, p. 53。<br />
117 See EMILIOU, 见前注 101, pp. 23-24。<br />
118 ANDENAS and ZLEPTNIG, 见前注 95, p. 388。
是否有利于此目的的实现。因此决策者面临的工作分为两部分,但是这两个部分为国家措施<br />
设置的标准很容易达到,这在国际投资仲裁中尤为如此。第一部分是查明所采取的措施是否<br />
符合合法目的。因此,非法目的在此阶段就可以被排除出去,因为它们从定义上就构成对相<br />
关权利和利益的不当干预。<br />
在国际投资仲裁中,大部分国家行为的公共目的都是合法的,只有在少数案件中才有必<br />
要基于比较的方法或国际条约的承认来评价目的的合法性。那些明显为了纯粹私利的腐败行<br />
为,或者诸如危害人类罪等明显违反强行法的国家行为,显然不是出于合法目的。但总体而<br />
言,很少有国家措施不符合某政府合法目的。<br />
在确定目的的合法性之后,决策者在第二部分必须确定所采取的措施是否有利于前述目<br />
的的实现。这就需要在“措施与目的之间确立因果关系”。 119 决策者因此必须确定所采取的<br />
措施能否促进既定目标的实现。同样,只有极少的措施不能通过适当性检验,因为政府的善<br />
意行为通常不会采取对实现既定目标完全无效的手段。<br />
2 必要性<br />
比例分析的第二步涉及到必要性的检验。其题中之义即确定是否存在其他对有关权利和<br />
利益侵犯较少并且同样能够实现既定目标却没有侵犯其他受保护利益的手段。必要性要求不<br />
存在同样有效但限制更少的措施。 120 这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是否存在限制更少的措施?<br />
第二,该措施是否同样有效且合理可行?这种检验的背景同样也出现在决策者平衡相互冲突<br />
的原则取得的最佳结果中。 121 如果相关权利原则上受到保护,那么就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允许<br />
国家超出必要的范围侵犯这些权利,因为还有其他同样有效的替代方法实现同样的目的。<br />
3 狭义上的比例原则<br />
比例分析的最后一步涉及到国家措施对相关权利和利益的影响同政府目的的重要性之<br />
间的平衡。狭义上的比例原则要求政府措施不超出所追求的目标并且对每一个原则都要进行<br />
相对的权衡。 122 对某个原则的违背或损害程度必须与其他原则的重要程度成正比。” 123 狭义<br />
比例原则要求对所有相关因素予以考虑,如成本收益分析,相关权利和利益的重要性,干预<br />
的强度(较大或较小),干预时间的长短(永久性或暂时性),是否存在效果较小但对相关权<br />
利限制较少的替代措施等等。<br />
必要性的分析最终可能会允许严格限制一项权利以保护某个微小的公共利益,因此第三<br />
个步骤是十分重要的。 124 此外,与那些更受欢迎的标准相比,前述推理的主要优点在于其要<br />
求法官或决策者将目的与相关权利的重要性联系起来,从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它要求决策<br />
者对那些可能取得更优结果的替代性政策予以积极地考虑,而不是仅仅评价其合理性,尽管<br />
后一种标准在政府制定政策时更受欢迎,但是其对相关权利的保护也更少。<br />
然而,这并不是说决策者应该用自己的偏好代替政府的选择,它仅仅意味着决策者应当<br />
考虑国家或政府的政策目标及其推理是否处于一个框架之内,该框架建立在对不同的、相互<br />
119 Jan H. JANS, “Proportionality Revisited”, 27 Legal Issues of Econ. Integration (2000) p. 239 at p. 240.<br />
120 同上。<br />
121 .Cf. Robert ALEXY,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p. 399.<br />
122 ALEXY, 见前注 87, 13 Ratio Juris p. 294, at p. 298。<br />
123 ALEXY, 见前注 86, p. 102。<br />
124 Rupprecht von KRAUSS, Der Grundsatz der Verhältnismäßigkeit in seiner Bedeutung für die Notwendigkeit<br />
des Mittels im Verwaltungsrecht (1955) p. 15 (指出“如果措施的合法性是唯一的要件(即最小限度的审查方<br />
法),那么一个微小的公共利益也能导致对权利的严重损害,而这却并不违法。”)。
冲突(即那些国家既要普遍保护又要最少干预的)的权利和利益的承认之上。例如,根据不<br />
同的解释上的问题和法律术语,决策者需要做的就是核实国家是否处在一个框架之外,该框<br />
架一边是对财产权和投资保护的承认,另一边则是合法的公共利益。<br />
(三)国际投资仲裁中比例分析的运用<br />
投资条约通过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间接征收的概念来要求对外国投资者利益的尊重,并<br />
以此确立了一个框架。当考虑一项监管措施是否在这个框架之中时,投资仲裁庭已开始逐渐<br />
运用比例分析。这在本节将要讨论的两组案例中尤为明显。其中一组关注的是如何在需要补<br />
偿的间接征收(其取决于所适用的条约或习惯国际法)和无需补偿的监管之间划定界限。另<br />
一组关注的是在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下,如果一项监管措施将促进与投资无关的利益并对投<br />
资者的期待利益产生不利影响,投资者的合法期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构成对该监管措施的阻<br />
碍。<br />
1 比例分析与间接征收的概念<br />
国际征收法是投资保护同相冲突的权利和利益短兵相接的一个领域。几乎所有的投资条<br />
约都有禁止无偿征收的规定。德国与中国的 BIT 中的一个典型条款规定如下:<br />
“除非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并给予补偿,缔约一方投资者在另一方境内的投资不得被直<br />
接或间接地征收,不得对其实行国有化或者采取具有征收、国有化效果的其他任何措<br />
施(以下称“征收”)。” 125<br />
征收不一定局限于涉及所有权从外国投资者向一国或者第三方转移的直接征收或国有<br />
化。根据条约规定或其他实践标准(例如习惯国际法),还可能包括所谓的间接征收、逐渐<br />
征收或事实征收,以及那些并不干预所有权,但是对财产本身有实质性的不利影响或使所有<br />
权人无法支配其财产的国家措施。 126 因此 NAFTA 的一个仲裁庭认为征收的概念:<br />
“不仅包括对财产公开,蓄意和公然的占有,例如直接没收或者将所有权正式或强制地<br />
125 《中国—德国 BIT》第 4.2 条。<br />
126 关于间接征收概念,参见 George C. CHRISTIE, “What Constitutes a Taking of Property Under International<br />
Law?”, 38 Brit. Yb. Int’l L. (1962) p. 307; Burns H. WESTON, “‘Constructive Taking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br />
A Modest Foray into the Problem of ‘Creeping Expropriation’”, 16 Va. J. Int’l L. (1975) p. 103; Rosalyn<br />
HIGGINS, The Taking of Property by the Stat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Law, 176 Recueil des Cours<br />
(1982) p. 259 at p. 322 et seq.; Rudolf DOLZER, “Indirect Expropriation of Alien Property”, 1 ICSID Rev. – For.<br />
Inv. L. J. (1986) p. 41; Thomas W. WÄLDE and Abba KOLO,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vestment Protection<br />
and ‘Regulatory Taking’ in International Law”, 50 Int’l & Comp. L. Q. (2001) p. 811; Catherine<br />
YANNACA-SMALL, “‘Indirect Expropriation’ and the ‘Right to Regulat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br />
OECD Working Paper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No. 2004/4, available at<br />
; Jan PAULSSON and Zachary DOUGLAS, “Indirect<br />
Expropriation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s” in Norbert HORN and Stefan KRÖLL, eds., Arbitrating Foreign<br />
Investment Disputes (2004) pp. 145-158; FORTIER and DRYMER, supra fn. 79, p. 293; Andrew NEWCOMBE,<br />
“The Boundaries of Regulatory Expropriation”, 20 ICSID Rev. – For. Inv. L. J. (2005) p. 1; Bjørn KUNOY,<br />
“Developments in Indirect Expropriation Case Law in ICSID Transnational Arbitration”, 6 J. World Inv. & Trade.<br />
(2005) p. 467; Charles LEBEN, “La liberté normative de l’etat et la question de l’expropriation indirecte” in<br />
Charles LEBEN, ed., Le contentieux arbitral transnational relatif a l’investissement international: nouveaux<br />
développements (2006) p. 163.
转到东道国,而且包括秘密或突然干预式的动用权利人财产,使所有权人无法对其全部<br />
或大部分财产予以使用,以及对合理预期的经济利益的剥夺,而前述措施并不要求东道<br />
国会明显获利”。 127<br />
传统的习惯国际法与条约法理论认为:直接征收与间接征收在国际投资条约下的唯一<br />
合法依据就是公共目的,而且必须以非歧视的方式实施并遵循正当法律程序。最为重要的是,<br />
直接征收与间接征收通常都要求补偿。 128<br />
东道国的监管行为也可能导致间接征收的发生。在仲裁判例中,对于如何区分需要补<br />
偿的征收与无需补偿的财产监管行为,不同的仲裁庭采用的基本方法也不同。 129 一些仲裁庭<br />
仅仅考虑东道国措施的影响,从而认为一项间接征收需要获得补偿是因为该措施的影响达到<br />
了一定强度,其要么对财产权利的重要部分施加了的永久干预, 130 要么对相关财产价值造成<br />
了实质性的减少或损害。 131 然而,在决定一项普通措施是否使得投资者有权根据间接征收的<br />
概念要求补偿时,大多数仲裁庭都会考虑该措施的目的,并引入一种“警察权力理论”。 132 警<br />
察权力理论认为国家在追求合法目的时有权力限制私人财产权且无需补偿。但根据这种方法<br />
还不足以确定一国措施的效果,因此必须将该措施的影响同其目标和目的进行权衡。<br />
127 Metalclad v. Mexico, 见前注 23, para. 103.<br />
128 关于间接征收的补偿标准是否不同的问题,参见 Yves NOUVEL, “L’indemnisation d’une expropriation<br />
indirecte”, 5 Int’l L. FORUM du droit int. (2003) p. 198; Thomas W. MERRILL, “Incomplete Compensation for<br />
Takings”, 11 N.Y.U. Envt’l L. J. (2002-2003) p. 110. Cf. also W. Michael REISMAN and Robert D. SLOANE,<br />
“Indirect Expropriation and Its Valuation in the BIT Generation”, 74 Brit. Yb. Int’l L. (2003) p. 115.<br />
129 See Udolf DOLZER, Eigentum, Enteignung und Entschädigung im geltenden Völkerrecht (1985) p. 186 et<br />
seq.; Rudolf DOLZER, “Indirect Expropriation: New Developments?”, 11 N.Y.U. Envt’l L. J. (2002-2003) p. 64<br />
with further references.<br />
130 See tarrett Housing Corp. v. Iran, AWD ITL 32-24-1, 19 December 1983, 4 Iran-U.S. Claims Tribunal Reports<br />
122, 154; Tippetts, Abbett, McCarthy, Stratton v. TAMS-AFFA et al, AWD 141-7-2, 22 June 1984, 6 Iran-U.S.<br />
Claims Tribunal Reports, 219, 225 et seq.; 关于伊朗—美国有关征收的仲裁案件,参见 George ALDRICH,<br />
“What Constitutes a Compensable Taking of Property? The Decisions of the Iran-United States Claims Tribunal”,<br />
88 A.J.I.L. (1994) p. 585.<br />
131 Phelps Dodge Corp. v. Iran, AWD 217-99-2, 19 March 1986, 10 Iran-U.S. Claims Tribunal Reports 121, 130;<br />
另见 SWANSON, “Iran-U.S. Claims Tribunal: A Policy Analysis of the Expropriation Cases”, 18 Case W. Res. J.<br />
Int’l L. (1986) p. 307 at p. 325 et seq.; WESTON, supra fn. 126, p. 103 at p. 119 et seq.。<br />
132 Maurizio BRUNETTI, “Indirect Expropri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5 Int’l L. FORUM du droit int. (2003) p.<br />
150; DOLZER, “Indirect Expropriation: New Developments?”, supra fn. 129, p. 64 at p. 79 et seq. (2002-2003);<br />
Rudolf DOLZER and Felix BLOCH, “Indirect Expropriation: Conceptual Realignments?”, 5 Int’l L. FORUM du<br />
droit int. (2003) p. 155 at p. 158 et seq.; Allen S. WEINER, “Indirect Expropriation: The Need for a Taxonomy of<br />
‘Legitimate’ Regulatory Purposes”, 5 Int’l L. FORUM du droit int. (2003) p. 166; Sea-Land Service Inc. v. Iran,<br />
AWD 135-33-1, 22 June 1984, 6 Iran-U.S. Claims Tribunal Reports 149, 165; Sedco Inc. v. NIOC and Iran, AWD<br />
ITL 55-129-3, 24 October 1985, 9 Iran-U.S. Claims Tribunal Reports 248, 275 et seq.; Too v. Greater Modesto<br />
Insurance Associat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WD 460-880-2, 29 December 1989, 23 Iran-U.S. Claims<br />
Tribunal Reports 378, 387 et seq.
尽管大多数投资条约并没有明确包括对财产保护的例外条款, 133 但是仲裁庭承认国家在<br />
追求合法目的时只要合理的平衡了该目的与监管措施对投资的影响便有权限制私人财产权<br />
利且无需补偿。因此,仲裁庭在 Tecmed v. Mexico 案中认为警察权力的例外构成了国际征<br />
收法律的一部分:“国家在其警察权力范围内行使主权权力,可能会对服从其权力的投资者<br />
造成经济损害,因为不论其行为是否存在争议,管理者都没有赋予投资者获得任何补偿的权<br />
利。 134 ”同样,在 Methanex v. United States 案中,仲裁庭强调<br />
“在一般国际法上,除非政府已向投资者明确承诺其将不采取特定的监管措施,否则出<br />
于公共目的而采取的非歧视性监管措施(即按照正当程序作出并影响投资者的行为的<br />
措施)将不被视作为征收且无需补偿”。 135<br />
然而,仲裁庭并没有对“怎样进行平衡”这一问题作出深入解释。Tecmed v. Mexico 案<br />
中仲裁庭在处理投资保护与相抵触的公共政策之间的紧张关系时采取的做法倒是充分体现<br />
了其对比例分析的运用。在该案中,墨西哥当局没有续签垃圾填埋场的临时营业执照,而这<br />
对于西班牙投资者在墨西哥子公司的业务至关重要。仲裁庭认为这构成了需要补偿的间接征<br />
收。在关于间接征收与监管的区别的论证中,仲裁庭参照了《欧洲人权公约》第一附加议定<br />
书第 1 条的相关判例,并运用和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相似的比例标准对相冲突的利益进行了<br />
权衡。<br />
有关机构拒绝续签垃圾填埋许可证的正当理由是经营者缺乏可靠性,尤其是填埋场含有<br />
经处理过的生物和其他有毒废物,使其违反了经营许可证的规定并且超出了垃圾填埋场的能<br />
力范围。 136 但是仲裁庭认为其中的政治性考虑因素是决定性的。 137 其指出,只是在 1997 年<br />
年底当地居民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之后,该机构才打算通过拒绝续签许可证来促使垃圾填埋<br />
场早日搬迁。 138 在投资者已经同意搬迁垃圾填埋场的情况下,该机构仍然拒绝了投资者续签<br />
133 例如这些通常包含在美国双边投资条约中的安全例外条款与类似的非排除措施条款会引发特殊的问题,<br />
这也不是本文要解决的。例如,见美国与埃及在 1986 年 3 月 11 日签订,于 1992 年 6 月 27 日生效的《美<br />
国——埃及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条约》第 10.1 条, (规定“本条约并不排除任一缔约方或其机构为维护其<br />
公共秩序和道德,履行其现有的国际法律义务,保护其自身安全利益,或者是为了履行其未来国际义务而<br />
采取任何必要措施,但该措施与其未来国际义务必须是适当的”)。关于这些条款的观点,参见 José E.<br />
ALVAREZ and Kathryn KHAMSI, “The Argentine Crisis and Foreign Investors: A Glimpse into the Heart of the<br />
Investment Regime” in Karl P. SAUVANT, ed., 1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Policy<br />
2008/2009 p. 379. 不同的观点,参见 William BURKE-WHITE and Andreas von STADEN, “Investment<br />
Protection in Extraordinary Times: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on-Precluded Measures Provisions in<br />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48 Va. J. Int’l L. (2008) p. 307。<br />
134 Tecmed v. Mexico, 见前注 24, para. 119。<br />
135 Methanex Corporation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NCITRAL/NAFTA) Final Award of 3 August 2005, Part<br />
IV - Chapt. D - para. 7. 类似地, International Thunderbird Gaming v. Mexico (UNCITRAL/NAFTA), 见前注<br />
37, para. 127; Saluka v. Czech Republic, 见前注 33, paras. 254-262; LG&E Energy Corp., LG&E Capital Corp.,<br />
LG&E International Inc.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2/1), Decision on Liability of 3 October<br />
2006, paras. 194-197; Feldman v. Mexico, 见前注 30, paras. 103-106。<br />
136 Tecmed, 见前注 24, paras. 99 et seq。<br />
137 Tecmed,同上,paras. 127 et seq。<br />
138 Tecmed,同上,paras. 106 et seq。
5 个月至搬迁时止的要求,并且命令投资者立即停止经营活动。 139<br />
在对上述事实适用间接征收概念时,仲裁庭将其分析分为两步。第一步,仲裁庭确定该<br />
项国家措施是否足以使无需补偿的监管转变为应予补偿的间接征收。仲裁庭认为这取决于两<br />
个因素:一个暂时性因素与一个永久性因素。首先,对于有关财产利益的干预不应当仅是过<br />
渡性的;其次,该干预必须导致财产价值的完全损害。由于垃圾填埋场的设施不能用于其他<br />
的目的,并且由于现存的污染使其不能被出售, 140 因此,不续签许可证的效果已经相当于征<br />
收。<br />
仲裁庭并没有就此结束分析。在第二步中,仲裁庭只是将不予续签经营许可证的效果当<br />
作区分监管与间接征收的因素之一。根据仲裁庭的观点,采取这种方法的原因源于一个原则,<br />
即国家在其警察权力范围内行使主权权力,可能会对服从其权力的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害,因<br />
为不论其行为是否存在争议,管理者都没有赋予他们获得任何补偿的权利。” 141 据此,仲裁<br />
庭认为双边投资条约原则上并不排除某项国家监管权力,即便其文本对于该权力的存在没有<br />
作出明确规定。因此,BIT 仅要求某具体国家措施对私人财产权的影响应当与国家警察权力<br />
的行使成比例。更为关键的是,仲裁庭因此认为即使条约的措辞没有明确提到警察权力这一<br />
例外,财产权也理应受到国家警察权力的约束和限制。<br />
按照基本权利推理的理论结构,仲裁庭运用了综合的比例检验来权衡相冲突的利益,以<br />
便确定合法的监管在何种情况下会转变为间接征收。仲裁庭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协调各类受影<br />
响的权利和利益。 142 从这个角度来看,只有国家措施对财产权利造成了不成比例的限制时,<br />
才构成需要补偿的间接征收。仲裁庭因此指出:<br />
“为了确定这些措施是否具有征收的特征,仲裁庭将考虑这类行为或措施对要保护的<br />
公共利益和法律赋予的投资保护造成的影响是否符合比例,因为这种影响的大小对于<br />
确定比例原则起着关键的作用。当对公共政策、社会利益以及保护利益的行为都造成<br />
影响的问题进行界定时,尽管仲裁庭的分析是建立在对国家应有的尊重之上,但这并<br />
不妨碍本庭根据墨西哥—西班牙 BIT 第 5 条第(1)款对国家的行为进行审查从而确定<br />
该行为采取的方法对于其目标以及被剥夺经济利益和合法期待利益的当事人而言是否<br />
合理。在强加给外国投资者的费用和负担与任何通过征收措施实现的目标之间必须有<br />
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为了对前述费用和负担进行评价,计算被国家行为剥夺的所有<br />
权大小以及确定是否对该剥夺给予了补偿是非常重要的。” 143<br />
139 See Tecmed,同上,paras. 45, 110 et seq。<br />
140 Tecmed,同上,para. 117。<br />
141 Tecmed,同上,paras. 118 et seq。<br />
142 “协调”(Konkordanz)或“实际协调”(praktische Konkordanz)是由德国宪法学家柯纳德·海塞创造<br />
的,它指的是一种调解的概念或方法,指不同基本权利间的平衡。在两种基本权利相冲突的情形下,“协调”<br />
追求的是在不放弃任何一方的情况下保持两种权利的和谐。这个概念否定将一种基本权利看做比其他权利<br />
要更高级。与区别对待两种权利来达成和谐不同,“协调”的任务是要运用比例分析在基本权利的背景下对<br />
不同的权利和利益予以权衡,从而为不同的权利提供最大程度的有效保护。参见 Konrad HESSE, Grundzüge<br />
des Verfassung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no. 72, 20th edn. (1995)。这一概念已被德国宪法法院认<br />
定为一项指导原则,见 BVerfGE 41, 29; BVerfGE 77, 240; BVerfGE 81, 298; BVerfGE 83, 130; BVerfGE 108,<br />
282。该概念也见于法国宪法委员会的宪法判例中 CC décision no. 94-352 DC, 18 Jan. 1995, available at :<br />
www.conseil-constitutionnel.fr/decision/1994/94352dc.htm。<br />
143 Tecmed, 见前注 24, para. 122。
仲裁庭在其平衡过程中所考虑的具体方面包括投资者的合法期待、东道国追求的监管利<br />
益的重要性、限制的程度和影响以及有关投资者的其他情况(例如所经营的公司先前对于经<br />
营许可证条款的违反)。 144 此外,仲裁庭在评价比例性时也非常关注采取的措施是否对投资<br />
者造成了特殊和不公平的影响。 145 综上所述,仲裁庭认为政府不予续签许可证不当地限制了<br />
申请人的财产权利,因此构成了间接征收。仲裁庭特别强调经营公司先前的违规程度是微小<br />
的,因此政府不能以此作为不予续签经营许可证的理由。<br />
此外,仲裁庭列举了一些其认为合理的财产权限制措施,从而对比例分析的一般方法予<br />
以了补充。例如用来消除公共安全威胁的强制措施,该措施一般直接针对威胁公共安全的个<br />
人,但在紧急情况下也会针对没有造成公共安全威胁的第三方。 146 所以,那些为了防止危险<br />
而采取的财产权干预措施是符合国际法的,而且不一定需要进行补偿。<br />
在 LG&E v. Argentina 案中,仲裁庭也采用了类似的比例分析。该案涉及阿根廷在其 2001<br />
年—2002 年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所通过的紧急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把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和索<br />
赔变成以阿根廷比索计价,以及影响外国投资在天然气和电力领域享有的关税担保。LG&E<br />
公司根据美国—阿根廷的 BIT 提出申诉,认为这些措施严重影响了其在阿根廷经营天然气<br />
业务的子公司的股权价值,因此构成了间接征收。 147<br />
但是,仲裁庭认为本案没有构成间接征收,因为其认定一项措施必须对投资产生了较高<br />
程度的干预才构成间接征收。仲裁庭认为,由股东提出的间接征收之诉的假定条件是“政府<br />
的措施已经使外国所有者的财产利益归于无效了。当权利人不能再控制其投资或者不能决定<br />
其投资的日常经营时,可以认定其所有权或收益权已归于无效。” 148 仲裁庭进一步强调,可<br />
以被认定为间接征收的干预通常都是永久性的措施。 149<br />
此外,仲裁庭认可 Tecmed v. Mexico 案中仲裁庭的方法,并运用了该案仲裁庭关于比例<br />
性和平衡的论证,以区分无需补偿的合法监管与需要补偿的间接征收。仲裁庭指出:<br />
“现在的问题在于究竟是应该只考虑措施产生的影响,还是也应考虑采取措施的背景与<br />
东道国的目的。本庭认为:为了证明一项措施具有征收的性质,必须对该措施的原因和<br />
影响进行一个平衡的分析。不要将政府采取征收措施的权力同其制定政策的权利予以混<br />
淆,这是十分重要的。‘前述决定是重要的,因为在国际仲裁庭的眼中,它是对一项监<br />
管措施(通常是指那些导致资产或权利减少的国家警察权力的行使)与实质性剥夺了资<br />
144 Tecmed,同上,paras. 149 et seq。<br />
145 Tecmed,同上,para. 122. 这个观点来自于德国一个关于限制利息的重要判例,即财产所有者是否要为了<br />
一般的公共利益而作出一项特殊的牺牲(“ 特殊受害者”)。参见 WÄLDE and KOLO, 见前注 126, p. 811 at p.<br />
845 et seq。<br />
146 Tecmed, 见前注 24, para. 136。<br />
147 See LG&E v. Argentina, 见前注 135, para. 177. 关于此案的裁决及其与 CMS v. Argentina 的比较分析,见<br />
Stephan SCHILL,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the Host State’s Power to Handle Economic Crises”, 24 J.<br />
Int’l Arb. (2007) p. 265。<br />
148 LG&E v. Argentina, 见前注 135, para. 188 (citing CME Czech Republic B.V. v. The Czech Republic<br />
(UNCITRAL), Partial Award of 13 September 2001, para. 604 and Pope & Talbot, Inc. v. The Government of<br />
Canada (UNCITRAL), Interim Award of 26 June 2000, para. 100).<br />
149 LG&E v. Argentina, 见前注 135, para. 193. 另见 LG&E v. Argentina, para. 191 (引用 Pope & Talbot, 见前注<br />
148, paras. 101 et seq.) (指出“如果投资还能继续运营,即使利润下降了,也不能算作是对投资者经营能力<br />
的干预。只有实质性的影响才能提起征收补偿请求”。)。
产或权利的事实征收进行区分的要素之一。’” 150<br />
因此,仲裁庭认为国际投资条约通常并不排除东道国在公共利益方面的监管权力。相反,<br />
它强调“国家有权采取具有社会或公共福利目的的措施”。 151 这一主张与一些国际法院和仲<br />
裁庭的观点是一致的,即一般而言,一国对其善意的监管行为无需承担国际责任。 152 然而仲<br />
裁庭同时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如果一项措施“明显有违比例”,即使其是为了公共利益而<br />
实施的普遍监管也需要给予补偿。 153<br />
近来的国家条约实践中也体现了类似的做法,例如美国近期的投资协议就包含对间接征<br />
收概念的解释:“如果缔约一方计划并实施的非歧视监管行为是为了保护合法的公共福利目<br />
标,如公共健康,安全与环境等,则不构成间接征收,除非其属于少数例外情况”。 154 这实<br />
质上是在间接征收概念的运用中引入了比例原则,因而有助于平衡投资保护与相互抵触的公<br />
共政策目的。<br />
2 比例分析和公平与公正待遇条款<br />
比例分析也可以适用于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的一些子元素中。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br />
不同的仲裁庭认为“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应当包含法律体制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东道国<br />
决策的一致性,对投资者信赖或“合法期待”的保护,程序上的正当程序与禁止拒绝司法,<br />
透明度的要求,合理性与比例性概念。 155 而适用这些一般性主张通常都需要权衡相互抵触的<br />
利益,需要确立审查、举证责任以及尊重程度的标准。<br />
例如,对于投资者合法期待的保护既不要求国内法律体制对任何补偿的要求都作出相应<br />
改变,也不要求其一成不变。相反,在实际适用公平与公正待遇的某些方面时,比例检验往<br />
往是必要的。 156 因此,仲裁庭在 Saluka v. Czech Republic 案中特别提醒到过于字面的理解投<br />
资者的期待是很危险的,因为这将会“强加给东道国不适当且不切实际的责任”。 157 仲裁庭<br />
随后在广义的比例检验范围内对投资者的合法期待与东道国的利益进行了平衡,其指出:<br />
150 LG&E v. Argentina, 见前注 135, para. 194 (引用 Tecmed v. Mexico, 见前注 24, para. 115).<br />
151 LG&E v. Argentina,见前注 135, para. 195.<br />
152 LG&E,同上,para. 196 (引用 American Law Institute, Restatement (Third)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Law of the<br />
United States, Vol. I (1987) Sect. 712, Commentary g, Too v. Greater Modesto Insurance Associates and The<br />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见前注 132, 23 Iran-U.S. Claims Tribunal Reports 378, 387 et seq. and The Oscar<br />
Chinn Case (United Kingdom v. Belgium), Judgment No. 23 of 12 December 1934, PCIJ Series A/B, Case No. 63,<br />
1934). Similarly, Sea-Land Service Inc. v. Iran, 见前注 132, 6 Iran-U.S. Claims Tribunal Reports 149, 165; Sedco<br />
Inc. v. NIOC and Iran, 见前注 132, 9 Iran-U.S. Claims Tribunal Reports 248, 275 et seq.; Methanex v. United<br />
States, 见前注 135, Part IV Chap. D, para. 7; International Thunderbird Gaming v. Mexico, 见前注 37, para. 123<br />
et seq.; Saluka v. Czech Republic, 见前注 33, paras. 253 et seq。<br />
153 LG&E v. Argentina, 见前注 135, para. 195 (引用 Tecmed v. Mexico, 见前注 24, para. 122).<br />
154 例见,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于 2003 年 1 月 15 日签订,2004 年 1 月 1 日生效,与间接<br />
征 收 概 念 的 范 围 的 变 化 有 关 , available at : www.ustr.gov/Trade_Agreements/<br />
Bilateral/Singapore_FTA/Final_Texts/Section_Index.html。<br />
155 见前文第 2 节 1—5。<br />
156 间接征收概念与公平与公正待遇项下合法期待的保护的主要区别是前者需要对财产利益或权利实行干<br />
预,而后者的范围更广并且能够包含某一监管或立法体制在持续运行中的期待。投资仲裁庭在关于其他问<br />
题的案件中也使用不同类型的平衡检验,其中就包括对保护伞条款的解释。<br />
157 Saluka v. Czech Republic, 见前注 33, para. 304。
“没有投资者会期待其投资时的有利环境会保持完全不变。为了确定对外国投资者的<br />
期待造成的损害是否正当与合理,必须对东道国为了公共利益而对国内问题进行监管<br />
的合法权利加以考虑。<br />
因此,要决定捷克共和国是否违反了第 3.1 条,一方面需要权衡申请人的合法与合理<br />
的期待,另一方面也要权衡被申请人合法的监管利益。<br />
受条约保护的外国投资者都会期待捷克共和国善意的实施其政策,即只要政策对投资产<br />
生了影响,那么该政策必须合理正当并且其行为没有明显违反一致性、透明度以及中立<br />
和非歧视的要求。尤其是,任何对于外国投资者的差别待遇不应当基于不合理的区分和<br />
要求,其必须与理性的政策之间具有合理的关系,而非是出于对其他非外商投资的偏<br />
好。” 158<br />
仲裁庭在 Saluka 案中的方法也被其他许多仲裁庭所认同。 159 然而更广泛的是,仲裁庭<br />
越来越多地将公平与公正待遇同合理性概念和比例性概念联系起来,以控制东道国对外国投<br />
资干预的允许程度。仲裁庭在 Pope & Talbot v. Canada 案中对于某行政机构行为合理性的评<br />
价, 160 以及 Eureko v. Poland 案中仲裁庭关于不能满足投资者期待的理由是否充分的分析,<br />
可以看作是在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的具体解释与适用中引入了合理性的一般概念。 161<br />
当仲裁庭审查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是否符合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时,与比例性有关的<br />
分析同样也可能发挥作用。在 Middle East Cement Shipping and Handling Co S.A. v. Egypt 案<br />
中, 162 涉及到扣押与拍卖申请人的船舶以偿还投资者对某国家实体的欠款。本案的关键问题<br />
是拍卖的程序是否有效实施,尤其是扣押通知是否已充分作出。 163 由于申请人并不在船上,<br />
政府根据其具有争议性的法律,以对船舶出具扣押通知书的形式作出了通知。然而,仲裁庭<br />
认为埃及当局错误地行使了自由裁量权,因为其是使用缺席通知而没有去申请人的本地地址<br />
直接通知申请人。在解释希腊——埃及 BIT 中征收条款的正当程序规定时,仲裁庭依据公<br />
平与公正待遇原则指出:“像扣押和拍卖申请人船舶这样重要的事项应当以直接联系的方式<br />
158 Saluka,同上,paras. 305 et seq。<br />
159 例见 BG Group Plc. v. The Republic of Argentina (UNCITRAL), Final Award of 24 December 2007, para. 298:<br />
“必须在投资者决定投资时所处的法律和经济框架下对东道国的义务进行审查。但如同阿根廷政府所<br />
称,这并不意味着对法律制度的冻结。相反,为了适应变化的经济、政治和法律情况,国家仍需保留<br />
其监管权力。正如其他仲裁庭在处理类似事项时指出,‘……还必须考虑东道国为了公共利益对其国<br />
内问题进行监管的合法权力’。”<br />
(引用 Saluka v. Czech Republic, 见前注 33, para. 304)。 另见 Feldman v. Mexico 见前注 30, para. 112 (指<br />
出“政府在行使监管权力时,为了应对变化的经济情况或者变化的政治、经济或者社会因素而经常改<br />
变其法律法规。这可能导致某种经济活动盈利减少或不能继续进行。”)。<br />
160 See Pope & Talbot v. Canada, 见前注 51, paras. 123, 125, 128, 155, 另见 MTD v. Chile, 见前注 27, para.<br />
161 See Eureko v. Poland, 见前注 36, paras. 232 et seq. 另见前注 39 中的论述与附带文本。<br />
162 Middle East Cement Shipping and Handling Co S.A. v. Arab Republic of Egypt (ICSID Case No. ARB/99/6),<br />
Award of 12 April 2002.<br />
163 这个问题引申出扣押是否违反了正当程序要求,即埃及—德国 BIT 中禁止不予补偿的直接与间接征收的<br />
规定,以及是否有违公平与公正待遇原则。
作出通知…而不论是否存在通过挂号信和回执进行通知的法律义务或实践”。 164<br />
虽然没有明确表述,但上述论证暗含着一个比例式分析,该分析对投资保护的重要性、<br />
所追求的合法政府利益、以及在通知上存在限制较少但同样有效的方法这一事实进行了权<br />
衡。<br />
(四)投资仲裁中的比例分析与推理<br />
比例分析正日益得到投资仲裁庭的适用,其适用方法与许多国内法律秩序和其他国际争<br />
端解决制度(如欧共体/欧盟,欧洲人权法院或者 WTO)相类似。比例分析首先涉及的就是<br />
决定东道国的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或违反了公平与公正待遇的某些方面。然而,比例分析<br />
也受到了公开的批评,其认为比例分析在平衡相冲突的权利和利益方面,赋予了法官作出受<br />
“政策驱动”的裁决的权力,批评还认为比例分析鼓励对原则的重视要高于规则。<br />
这种批评在国内背景下可能不算太大的问题,因为国内立法机关有权力(至少对于将来<br />
的判决)推翻法院关于行政和立法标准的决定。然而,在投资条约背景下,双边投资条约的<br />
修订是一个程序和效果上都很缓慢的过程,它需要缔约国双方的一致同意。此外,大部分投<br />
资条约都没有一套修改的制度程序来针对投资仲裁庭的解释,例如根据 NAFTA 自由贸易委<br />
员会,缔约国可以通过该机构共同颁布对于投资争端规则和标准的权威解释。 165 虽然对比例<br />
分析的适用在宪法性权利方面与投资条约项下投资者的权利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但与特设的<br />
或临时的投资条约仲裁庭相比,那些国家宪法法院和依据条约设立的国际法院,例如欧洲法<br />
院与欧洲人权法院,有着更好的制度来承担这一责任。<br />
然而正如本文所述,在涉及重要公共利益的情形下,投资条约仲裁庭已经在行使着治理<br />
职能并适用着非常开放性的标准。鉴于这一现实,连同其他仲裁庭的制度性监督与审查,以<br />
及学术界、智库与非政府组织的严格审查这样的松散控制结构,对比例方法的采用在最低限<br />
度上建立了标准和框架,以用来确保仲裁庭根据相关原则考虑相关利益,并且根据既定的框<br />
架对这些利益予以权衡。这可能会使仲裁庭作出更好和更有说服力的论证,并使对仲裁庭的<br />
评价、批评和责任变得更加清晰,因为在比例原则的框架和方法下,每一个决定都必须是合<br />
理的。在广泛总结案件事实之后便基于“只要我看到,我就知道”式的推理对一国措施是否<br />
违反公平与公正待遇或者是否构成征收而作出的唐突决定,该决定当然不具有清晰的法律推<br />
理,而与这种方法相比,比例分析作为一种平衡投资保护与相互抵触的利益的理性方法,似<br />
乎更为可取。<br />
比例分析的优点还在于其能够开放适用于不同的政治理论以及不同的投资保护上的偏<br />
好。 166 有些人主张仲裁庭应当更全面的考虑受裁决结果影响的非缔约方的与投资无关的利<br />
益,另一些人则主张缩紧国家干预外国投资的法律体制,比例分析对于这两类主张都有吸引<br />
力。此外,比例分析的方法论结构可能使仲裁员变得更加负责,因为他们必须详细地说明其<br />
164 Middle East Cement Shipping v. Egypt, 见前注 162, para. 143。<br />
165 参见 NAFTA 第 1131(2)条。关于这一条款的解释,参见 NAFTA Free Trade Commission, Notes of<br />
Interpretation of Certain Chapter 11 Provisions, 31 July 2001, available at<br />
www.international.gc.ca/trade-agreements-accords-commerciaux/disp-diff/NAFTA-Interpr.aspx?lang=en。同样,<br />
美国 BIT 新范本也规定了一个类似的以条约为基础的机构。见美国 2004 年 BIT 范本 30(3) 条:“缔约方的<br />
联合声明,为了本条的目的,每一方都应通过其指定的代表行事,声明他们对于本条约规定的解释对于仲<br />
裁庭有约束力,仲裁庭所作出的任何决定和裁决应当与联合声明保持一致。”<br />
166 Cf. ANDENAS and ZLEPTNIG, 见前注 95, p. 371 at p. 387, drawing on the work of Paul Craig on judicial<br />
review of agency decisions in the United Kingdom。
裁决的正当理由。比例分析因此可以成为一个加强政府行为和仲裁庭活动的问责性和正当性<br />
的工具。<br />
总之,尽管存在犹豫的原因,但是比例原则有助于构建国家与外国投资者之间以及国家<br />
与投资仲裁庭之间的关系。对比例原则的使用可能增强了那些受规则支配的法律机构的合法<br />
性。一项关于越来越多的国内法院和国际法院运用比例分析的研究指出:“通过运用比例原<br />
则,宪法法官掌握了应对这些基本合法性问题的一致、切实可行的方法。” 167 关于国际投资<br />
条约法律制度合法性的强烈关注促使人们将比例分析作为一种标准方法大加运用。这能进一<br />
步促使投资仲裁庭认识并满足针对其在全球监管治理中的地位提出的要求。<br />
四、应对国际投资仲裁制度的合法性要求:全球行政法的作用<br />
仲裁庭在为东道国针对外国投资者的行为制定标准以及在审查东道国是否违反这些标<br />
准时行使着重大的权力。正如本文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所示,当作为治理制度的一部分时,<br />
这种权力也被扩大了。许多学者和实务工作者指出应当关注这些权力运行的合法性,甚至有<br />
人声称“合法性危机”已经或不久就会发生。 168 本部分第一节内容着眼于增强合法性的要求<br />
与前文所述的国际投资仲裁的治理功能之间的联系,并且建议进行一些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被<br />
决策者自身所执行的改革。通过使得仲裁庭以及其他机构的做法更加符合适用的新兴全球行<br />
政法的原则,这些改革能够增强合法性。本部分第二节内容认为,在进行这项改革中一个特<br />
别重要的要素是仲裁庭、仲裁庭任命和监管机构应当确保仲裁庭在法律解释,分析与推理上<br />
的质量和深度。<br />
(一)国际投资仲裁庭作为超越国家的监管者:区分不同的合法性问题<br />
民主社会的人们习惯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在公共事务方面的权力行使,尤其是由公共机<br />
构或者经国家授权可处理公共事务的机构行使公共权力时应当合法。这种观念对于在公共领<br />
域内行使权力的国际投资仲裁庭同样适用:它们审查国家过去的行为,它们有助于对国家将<br />
来的行为设置限制,他们也在影响全人类的事项以及对这些人们的管理方式上确定了立场。<br />
仲裁庭在全球行政空间内运行并行使着权力,全球行政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国家间的协<br />
议建立的,这些协议包括投资条约和《ICSID 公约》,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以及 1958 年的<br />
《纽约公约》。因此,对这些国际投资仲裁庭的公共合法性以及正当性的要求与适用于商事<br />
仲裁的要求有所差别,而且往往差别显著。公司之间普通的跨国商事仲裁在合法性要求方面<br />
是一种不同的争端解决形式。然而,投资条约仲裁面对的合法性要求源于其对于东道国行为<br />
的控制,其所针对的东道国行为是在公共领域实施的而不是在私人领域实施的,而商事仲裁<br />
案例通常只对争端当事人与其利益相关者具有重要意义,尽管这些案例有时也具有先例甚至<br />
是系统性的影响。 169<br />
167 STONE SWEET and MATHEWS, 见前注 96, p. 5。<br />
168 参见文章引用的前注 7。<br />
169 关于投资仲裁与普通商事仲裁之间的区别,参见 Gus VAN HARTEN and Martin LOUGHLIN, “Investment<br />
Treaty Arbitration as a Species of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17 Eur. J. Int’l L. (2006) p. 121 at p. 139 et seq.;<br />
Stephan SCHILL, “Arbitration Risk and Effective Compliance: Cost-Shifting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7<br />
J. World Inv. & Trade (2006) p. 653, at pp. 676-679.商事仲裁的相关经验对于经济主体的判断有系统性影响,<br />
即决定在将来的合同中是否应当包括仲裁条款以及应该使用哪一个仲裁机构和仲裁规则。Loukas<br />
MISTELIS, Crina BALTAG, Stavros BREKOULAKIS, Corporate Attitudes and Practice: Recognition and<br />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wards (2008); Loukas MISTELIS,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orporate Attitudes and
人们可以通过“韦伯”式的方法理解和实现合法性,也可以通过民主选举程序或者合理<br />
的替代程序以民主的方法理解和实现合法性。下面将会对这两种实现合法性的不同方法进行<br />
简要介绍。马克思·韦伯认为法律与机构的合法性(即在强迫服从之外对权力的诉求)主要<br />
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惯例(例如一种被长期接受的行为方式)、有魅力的领导或者官僚机<br />
构的理性。 170 在普通人看来,国际投资仲裁庭几乎没有惯例,他们很少依赖于公众形象和<br />
其成员的个人魅力。因此,在韦伯式方法中,国际投资仲裁庭至少部分依赖于其设计和程序<br />
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以及仲裁庭在解释与证明其裁决时给出理由的质量和说服力。该问题<br />
将在第二节进行讨论。<br />
民主选举制度提供了一个不同且更详细的合法性方法。 171 记名投票民主选举的特点之一<br />
在于它赋予选民以特殊的民主自由,使他们能够任意行使选举权从而参与政治表达。投票者<br />
无须说明他们选择的理由,仅仅出于对当前政府的厌倦,他们就有权对其进行否决。 172 因此,<br />
政府民主形式基本的合法性就是通过自主选民的投票选举而获得的。当选的领导人随后也可<br />
以赋予他们所组建、掌管或支持的国际组织以合法性,其中也包括那些他们可以行使任意性<br />
的政治权力(如将一个内阁部长或政府机构的负责人免职)的机构。然而,将这种民主合法<br />
性扩展到正式的跨国机构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实力相对较弱且对这些机构的影响<br />
力十分有限的弱小国家而言。 173<br />
因此,国际投资仲裁庭的直接民主合法性是脆弱的。他们基于有关国家的同意,其要么<br />
是通过 BIT 或区域性协定或《ICSID 公约》以公开的方式作出,要么是在具体问题上由一国<br />
机构与投资者在合同中私下作出。然而,仅仅通过这样的授权通常还不足以为仲裁庭的决策<br />
权提供足够的民主合法性。条约性的约定长期存在,它们并不受具有民主政治参与程序的机<br />
构的监督,并且当投资者的仲裁请求已经作出且仲裁庭已经开始仲裁时,那些在民主国家中<br />
赋予政府机构以基本合法性的选举程序很少能够发挥作用。而且,东道国常常自己决定对于<br />
仲裁庭中某位仲裁员的任命而无须与作为申请人的投资者协商。<br />
因此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行使公共权力的跨国机构(包括国际投资仲裁庭)的非选举机<br />
制的合法性是什么?非选举机制的合法性对于各种跨国机构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对<br />
于那些拥有实际管理权力,能影响到私人、公司、国家以及其他组织的权利和义务的跨国机<br />
构。实际上,对于合法性、有效性与行为正当性的关注,加上政治上的压力和抗议,许多跨<br />
国机构已改变了他们的做法和观点,使其符合自身的合法性规则以及与公共事务有关的监管<br />
机构和公共角色的作用。例如,巴塞尔委员会就商业银行监管问题采取新政策之前,在网上<br />
Practices”, 15 Am. Rev. Int’l Arb. (2004) p. 525; Theodore EISENBERG, Geoffrey MILLER and Emily<br />
SHERWIN, “Arbitration’s Summer Soldiers: An Empirical Study of Arbitration Clauses in Consumer and<br />
Nonconsumer Contracts”, 41 U. Mich. J. L. Ref. (2008) p. 871. 对于仲裁庭来说,以合同为基础的国际投资仲<br />
裁的公共合法性问题通常与以投资条约为基础的国际投资仲裁的情形是一样的。参见 José ALVAREZ, “Book<br />
review”, 102 AJIL (2008) p. 909, at pp. 911-2。<br />
170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br />
eds., 1968).<br />
171 See John FEREJOHN, “Accountability in a Global Context”, <strong>IILJ</strong> Working Paper 2007/5 (Global<br />
Administrative Law Series)available at:http//iilj.org/publications/documents/2007-5 GAL Ferejohn.web.pdf.<br />
172 同上,p. 20 et seq. (讲述了一个古希腊故事,即一个农民投票放逐阿里斯蒂德斯(Aristides),仅仅因为<br />
该农民已经受够了把他称为“正义”)。<br />
173 Grainne de BURCA, “Developing Democracy Beyond the State”, 46 Columbia J. Transnat’l L. (2008) p. 221.
发表了草案并征求意见; 174 世界银行在制定其社会保障措施时也遵循类似的咨询程序,并且<br />
设立一个检查小组来处理个人以世界银行违反自身政策行为的受害者身份而提出的控告; 175<br />
《ICSID 公约》目前也在考虑投资仲裁中的文件以及开庭程序的透明度问题,这在几年前还<br />
是不能想象的。 176<br />
这些发展虽然不是全球性的,但也不是孤立的改革。他们是全球行政法的基本规范(在<br />
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下)的一部分,这些规范用于解决诸如参与、透明度、正当程序、论证的<br />
理由、审查机制的存在、问责性以及对法治等基本公法价值的尊重这些问题。 177 全球行政法<br />
的这些规范在特定情形下是可以作为成文法予以适用的。然而,在确定其他决策机构(例如<br />
某国内法院)对于案件中所涉国际机构的规则或决定的重要性时,这些规则通常也有影响力。<br />
更抽象地说,在构建关于跨国机构行使影响人类生活和福祉的权力合法性的辩论中,这些规<br />
范是一种尺度。<br />
在国际投资仲裁中,被申请国及其民众对仲裁程序的实际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民<br />
主合法性,因为当选政府参与了其同意成立的仲裁庭的成员指定并且对其案件进行答辩。然<br />
而,当仲裁庭解释那些不太明确的并因此使仲裁庭拥有很大决策空间的条款时,例如“公平<br />
与公正待遇”标准或者间接征收概念,前述情况就远远不够了。由于仲裁庭关于如何解释和<br />
适用某个开放式规定的裁决可能对非参与者产生影响,这包括全世界很多国家和无数的具体<br />
174 Michael BARR and Geoffrey MILLER,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The View from Base”, 17 Eur. J. Int’l L.<br />
(2006) p. 15.<br />
175 Benedict KINGSBURY, “Operational Policies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s Part of the Law-Making Process:<br />
The World Bank and Indigenous Peoples” in Guy S. GOODWIN-GILL and Stefan TALMON, eds., The Reality of<br />
International Law (1999) p. 323; David SZABLOWSKI, Transnational Law and Local Struggles: Mining<br />
Communities and the World Bank (2007).<br />
176 见修改后的《ICSID 仲裁规则》: 第 48.4 条(涉及公布仲裁庭的法律论证; 第 37.2 条 (涉及第三方法律<br />
顾问的身份参与庭审); 第 32.2 条(涉及进行公开庭审程序的可能性)。关于《ICSID 仲裁规则》的新近修改<br />
见 Aurélia ANTONIETTI, “The 2006 Amendments of the ICSID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Additional<br />
Facility Rules”, 21 ICSID Rev. – For. Inv. L. J. (2007) p. 427。 关于投资仲裁中透明度和第三方参与的更多问<br />
题见 Jack J. COE, “Transparency in the Resolution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s – Adoption, Adaptation, and NAFTA<br />
Leadership”, 54 U. Kan. L. Rev. (2006) p. 1339; Carl-Sebastian ZOELLNER, “Third-Party Participation (NGO’s<br />
and Private Persons) and Transparency in ICSID Proceedings” in Rainer HOFMANN and Christian J. TAMS, eds.,<br />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ICSID) – Taking Stock After 40 Years<br />
(2007) p. 179; Christian J. TAMS and Carl-Sebastian ZOELLNER, “Amici Curiae im internationalen<br />
Investitionsschutzrecht”, 45 Archiv des Völkerrechts (2007) p. 217; Christina KNAHR, “Transparency, Third Party<br />
Participation and Access to Document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23 Arb. Int’l (2007) p. 327。 然而<br />
值得注意的是,对《UNCITRAL 仲裁规则》的修改要慢得多,而且某些仲裁当事人更倾向于那些目前仍远<br />
离公众视线的诉讼场所.<br />
177 关于全球行政法具体原则的实质性论述,参见前注 2 以及 12—16 所引用的材料,以及 Jean-Bernard<br />
AUBY, Armin von BOGDANDY, Sabino CASSESE, Richard STEWART, 以及该领域其他顶尖学者的成果,基<br />
本参考书目见。另一项有价值的分析见 Robert HOWSE, “Adjudicative Legitimacy and<br />
Treaty Interpret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The Early Years of WTO Jurisprudence” in Joseph WEILER, ed.,<br />
The EU, The WTO and the NAFTA: Towards a Common Law of International Trade (2000) p. 35, 关注公平程序,<br />
法律解释的一致性和完整性,以及对其他相关国际法律制度(如国际环境法律制度)的敏感度,这些被<br />
WTO 上诉机构用来作为构建自身合法性的要素。
投资,因为实际上在每一个投资条约关系中都含有同样的或类似的条款,因此情况会变得更<br />
为复杂。仲裁庭对于此类条款的解释可能影响国家及其立法机关和行政机构今后的行为,以<br />
及投资者的预期和选择,或许还会影响与投资有关问题的其他主体。换句话说,投资仲裁庭<br />
作出的公开裁决的影响不仅仅限于受投资条约调整的正在处理的争端。在国际投资条约仲裁<br />
中对先例重要性的研究和对先例的普遍适用,以及投资条约本身的措辞中,尤其可以看见这<br />
种情况。 178<br />
仲裁庭对于全球行政法原则(这些原则适用于仲裁庭的工作)的遵守能够对产生并且/<br />
或者增强投资条约仲裁的合法性产生作用。反之,无视这些原则将为严重批评仲裁庭的工作<br />
提供理由。本文第二部分内容主要通过对外国投资者享有的公平与公正待遇义务的解释,分<br />
析了仲裁庭的判例如何为国家界定一个基于良好治理和法治标准的制度框架。通过研究从公<br />
平与公正待遇中得出的国家良好行政行为的要求,并将这些研究作为权衡国家行为合理性的<br />
标准,也适当地提醒人们仲裁庭自身有时也没有符合他们认为公平与公正待遇应有的透明<br />
度、可预见性、说明裁决理由以及利益受影响者参与的要求。当然,仲裁庭并不是国家,在<br />
适用条约时不能在形式上和国家实行同样的标准。然而,随着全球行政法的不断发展,国际<br />
投资仲裁庭对国家适用的各种要求,也日益成为适用于其自身运行的法律措施的指标。<br />
对于国际投资仲裁庭来说,最关键的全球行政法原则显然包括:正当程序、合法性、在<br />
裁决过程中杜绝偏见或者任意性。由一个可信的独立机制充分审查仲裁庭工作的规定,虽然<br />
因其会带来程序拖延和较高成本而难以成型,但其在将来是不可避免的。当对仲裁员的指定<br />
受到合理质疑或者有人主张仲裁员与案件有直接利益冲突时,由仲裁员或者任命机构独立理<br />
性地对裁决进行审查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存在。独立性对合法性是非常<br />
重要的,这是因为人们要求仲裁庭解决问题并说明其决定和裁决的理由,而这在对仲裁庭裁<br />
决进行实质性审查时也是如此。人们期待民主国家的法院就其判决给出令人信服的法律依<br />
据,部分是因为法院本身并不直接对公众负责。如果公众足够地相信第三方,那么仲裁当然<br />
可以建立在信赖之上,即便没有指明太多规则,也不要求更多的论证,公众也可能愿意将决<br />
策权交予第三方。当是,当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恶化到需要寻求仲裁解决时,前述情况<br />
还是比较少见的。当缺少这种信任或对合法性的更多关注时,适用的法律规则通常由政治程<br />
序加以严密规定,争端解决机构给出的理由也具有更大的意义,因为其做出的裁决必须与预<br />
先规定的法律相一致。本文的下一部分将对于仲裁庭“说理”的实践与规范以及近期国际投<br />
资仲裁中仲裁庭援引其他仲裁庭裁决的现象进行探讨。<br />
(二)系统性合法的要素——充分分析和考虑其他裁决<br />
作为对争议双方的理由和事实主张的回应,推理过程是重要的。对于可能反复作为被告<br />
的国家以及那些非诉讼当事人,推理过程也很重要。因为推理过程是仲裁裁决的一部分,随<br />
着仲裁庭日益遵循普通法的法理,并适用大量基于投资仲裁先例的推理结构,仲裁裁决将指<br />
导今后的行为,也将为更广泛的受众塑造规范性的期待。这种对观念和结构的影响就是投资<br />
仲裁庭作为监管者的核心所在。<br />
因此,不论是对于非选举仲裁庭的合法性,还是对于国家将来的行政与监管行为和监管<br />
影响来说,仲裁裁决的推理都相当重要。《ICSID 公约》第 48.3 条明确规定“裁决应当说明<br />
其所根据的理由。 179 然而,这并没有真正说明要求给出推理过程的目的。而且,裁决撤销委<br />
178 参见下注 183 及附带文本。<br />
179 根据《ICSID 公约》第 52.1(5)条,未陈述裁决所依据的理由也构成取消 ICSID 裁决的理由之一。同<br />
样,其他仲裁规则也明确规定裁决必须说明理由, 例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第 32.3 条(然<br />
而此处也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同意不陈述理由)。
员会为避免裁决被撤销而对推理过程的质量或说服力制定相对合理的标准,在其最近的决定<br />
中却并没有将推理过程的要求置于公共理性,协商民主以及合法性的大背景之下。相反,他<br />
们主要关注争端当事方能否接受其推理,至于推理是否更多的为听众所理解(例如立法机关、<br />
法院、受裁决影响国家的公众以及利益可能受裁决影响的不相关国家的公众、无关的投资者、<br />
保险公司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这并非必要。 180<br />
正如本文开头部分所指出,全球行政法实现全球治理过程的涵义之一就是裁决的推理和<br />
投资仲裁争端中的司法判例应该反映法律的公共性特点,它不能仅针对仲裁的各方,使他们<br />
了解裁决的判决理由,而且应当针对没有代表和未参与仲裁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情况和利<br />
益。特别是,当影响到国际投资法和仲裁的一般原则时,仲裁中的推理必须要应对这些更广<br />
泛的体制性问题。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对每个这样的问题都作出肯定的陈述,因为谨慎、细心<br />
和简约都是仲裁和司法所需的优点。然而,推理过程应该是透明的,其不仅是从当事方的角<br />
度出发,而且应着眼于更广泛的受众,包括非参加国,投资团体和那些可能被针对外国投资<br />
活动的决定影响的群体。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在实践中,先例对投资裁决的影响是真实存<br />
在的。<br />
人们有时认为投资仲裁庭通常不具有先例的权威,因为仲裁庭只能决定手中的现有案<br />
件,而且每个案件都是新的情况,因此仲裁庭无需担心自己的先前裁决对被申请国将来行为<br />
的调整性影响,更不用说对其他的国家了。 181 无论前述观念从法理上,还是从减少各个仲裁<br />
的裁决之间的差距和冲突并且消除合法性问题的理论机制方面来说有多少优点,这都不是当<br />
前的实践做法。如果在决定如何处理特定的外国投资时不考虑关于这类具体问题的仲裁裁<br />
决,那么国家及其法律顾问的做法就是轻率的。在国家实践的变化之中,如国家起草新的投<br />
资条约或者修改现有条约时,对投资条约裁决的关注也十分明显。例如,公平与公正待遇及<br />
间接征收概念的宽泛解释使得美国在最近缔结的一些双边投资条约和自由贸易协定中使用<br />
了更为严格的措辞。 182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各国认为先前判例已具备事实上的规制力。<br />
180 尽管给出理由不意味着没有任何缺漏,但推理必须使“读者能有所遵循”,参见 CMS Gas Transmission<br />
Company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1/8), Decision of the Ad Hoc Committee on the<br />
Application for Annulment of the Argentine Republic of 25 September 2007, para. 97; 另见 Wena Hotels Ltd. v.<br />
Arab Republic of Egypt (ICSID Case No. ARB/98/4), Decision on the Application by 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br />
for Annulment of the Arbitral Award of 28 January 2002, para. 81。<br />
181 例如,在 RosInvestCo v. Russia 案中,仲裁庭在不接受先例时采取了这一策略,这些先例与最惠国待遇<br />
条款(MFN)能否引入更广泛的管辖权相关,这是东道国基于其与第三国之间的投资条约所作出的。参见<br />
RosInvestCo UK Ltd. v. The Russian Federation (SCC Case No. V 079/2005), Award on Jurisdiction, October 2007,<br />
para. 137 (由于关于 MFN 条款的解释存在公开的异议:<br />
“经过对其他仲裁庭关于 MFN 条款的裁决与其他条约的仲裁意见的研究,仲裁庭认为没有必要对这些<br />
决定进行详细论述。仲裁庭同意当事人的观点,即从前述决定中确实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取决于<br />
在允许推论的情况下如何评价仲裁条款与 MFN 条款的不同措辞以及它们的相似之处。然而,由于本<br />
仲裁庭的主要职能是对当前案件作出裁决,而不是进一步发展 MFN 条款对争端解决规定的可适用性<br />
的一般论述,所以本庭认为:本案 BIT 中的 MFN 条款与仲裁条款中的混合措辞与其他裁决中涉及的<br />
任何条约的措辞都不相同。”)。<br />
182 例如,为了与先前条约中的宽泛用语相区别,《美国—多米尼加共和国—中美洲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br />
(www.ustr.gov/Trade_Agreements/Bilateral/CAFTA/Section_Index. html)第 10 章第 5.2(a)项规定“公平与<br />
公正待遇的义务包括:不得拒绝刑事、民事或行政司法程序中的正义,这些是与世界主要法律制度中的程
近来几乎所有的 ICSID 和 NAFTA 的管辖权决定和对案情的裁决都引用了 ICSID 的裁<br />
决。最近的一项对投资仲裁庭引用先前裁决 183 的定量研究在阅读了新近的裁决后证实了一个<br />
强烈的倾向,即“对所谓的次要渊源的援引,其中包括司法判例和仲裁裁决,而仲裁裁决是<br />
占主导地位的”。 184 对先前裁决的引用是很重要的,而先前裁决对以后的裁决也会起到一定<br />
的影响,投资仲裁庭作出的关于先前裁决价值的论述中也表明了这一观点。虽然他们也强调<br />
缺乏遵循先例的法律依据,但他们却不可遏止地在先前裁决中寻求指导。 185 例如,在 El Paso<br />
v. Argentina 案中,仲裁庭表明将“遵循和先前裁决同样的路线”,因为当事人双方在其书面<br />
诉状和口头辩论中已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先例。 186 争端当事方依赖先例解决争端的方式由此暗<br />
示了一种趋势,即仲裁庭作出裁决并不是通过抽象地解释 BIT 对案件作出裁决,而是将其<br />
置于已经存在的投资条约裁决所论述的内容和结构之中。 187<br />
序正义原则是一致的。”另见《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2003 年 1 月 15 日签订,2004 年 1 月 1 日生<br />
效)第 15.6 条,本款涉及关于间接征收概念范围的换文,其声明善意的一般监管不必然构成可补偿的间接<br />
征收。关于投资仲裁和投资条约实践关系的更多论述见 UNCTAD,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and<br />
Impact on Investment Rulemaking (2007) pp. 71-89。<br />
183 Jeffrey P. COMMISSION, “Precedent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 A Citation Analysis of a Developing<br />
Jurisprudence”, 24 J. Int’l Arb. (2007) p. 129 at pp. 142-154.<br />
184 同上,at p. 148。 他的结论表明“ICSID 仲裁庭对 ICSID 先前裁决的引用明显增多”(同上,at. p. 149)。<br />
在 1990 到 2001 年间,ICSID 每个仲裁庭平均引用了两个之前 ICSID 的裁决或决定,而在 2002 年至 2006<br />
年间,则增加到了七个之多。关于管辖权的 ICSID 裁决甚至引用之前裁决多达九个。同样的趋势也出现在<br />
ICSID 下附属机构和非 ICSID 投资协定的仲裁裁决中。(见表 3-5,同上,at pp. 149-150)。<br />
185 另见 Gabriele KAUFMANN-KOHLER, “Arbitral Precedent: Dream, Necessity or Excuse?”, 23 Arb. Int’l<br />
(2007) p. 357。<br />
186 El Paso Energy International Company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3/15), Decision on<br />
Jurisdiction of 27 April 2006, para. 39. 另见 AES Corporation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br />
ARB/02/17),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of 26 April 2005, para. 18 (指出:投资者像援引先例那样不同程度地依赖<br />
先前的投资裁决,并且声明阿根廷对于仲裁庭管辖权的异议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相同的或者类似的案<br />
例对于此类管辖权异议已经给出了确定的答案”)。<br />
187 关于先例的援引、适用以及证明偏离先例正当的期望的出现,参见 Appellate Body Report, Japan – Taxes<br />
on Alcoholic Beverages WT/DS8/AB/R, WT/DS10/AB/R, WT/DS11/AB/R, adopted 4 October 1996, p. 14 (指出<br />
“已通过的专家组报告是 GATT 法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常常被此后的专家组所考虑。它们在 WTO<br />
成员中产生了合法期待,因此在与它们有关的任何争端中都应当予以考虑。但是除了解决争端各方之间的<br />
具体争端以外,它们没有约束力。”). Similarly Saipem S.p.A. v.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Bangladesh (ICSID<br />
Case No. ARB/05/07),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and Recommendation on Provisional Measures of 21 March 2007,<br />
para. 67<br />
“仲裁庭认为其不受先前裁决的约束,同时也认为其必须对国际仲裁庭先前的决定予以适当考虑。本<br />
庭认为,面对相反却都令人信服的论据,其有责任采用在许多相似的案件中所确定的解决方案。本<br />
庭同时认为,面对既定条约的细节及案件的事实情况,其有责任促进投资法律的和谐发展,从而满<br />
足国家社会与投资者对于法治确定性的合法期待。”<br />
另见 International Thunderbird Gaming v. Mexico,见前注 37, Thomas Wälde 的个别意见, para. 16 (指<br />
出:尽管仲裁裁决自身尚不能构成有约束力的先例,但持续一致的推理路径发展了特定条约义务的<br />
特定解释和原则,这一点应该予以重视。如果一个权威性判例已出现,那么它将具有习惯国际法的
先例的重要性在 NAFTA 的 Waste Management v. Mexico 案裁决中尤为明显,该裁决自<br />
身就综合了 NAFTA 的先例,其目前已成为 NAFTA 的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和其他 BITs 中的<br />
类似标准的经典案例。与“遵循先例”(stare decisis)的风格类似,仲裁庭通过参照先前 NAFTA<br />
的裁决从而界定了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并指出:<br />
“总的来说,S.D. Myers 案、Mondev 案、ADF 案 与 Loewen 案都表明,如果某个国家行<br />
为是任意的、极不公平、不公正或特殊的、歧视性的,并使得申请人遭受到地域或种族<br />
歧视,或者是缺乏正当程序而造成了违反司法正当性的结果(可能是在司法程序中明显<br />
缺乏自然正义或在行政程序中完全缺乏透明度和公正性),那么这一有害于申请人的行<br />
为违反了公平与公正待遇的最低待遇标准”。 188<br />
因此,仲裁庭主要从先前的裁决中总结出公平与公正待遇的含义,并据此对该标准进行<br />
定义,而不是根据其自身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文本的解释。因此,在 Waste Management<br />
案中,仲裁法庭本身更注重于从具体案件的事实中衍生出的标准。 189<br />
一旦承认仲裁庭的法律解释和推理对于以后的仲裁庭和国家,以及在缔约国和非缔约国<br />
中裁决的合法性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实践问题,那么推理过程在实践中的问题也就随之显<br />
现了。问题之一便是仲裁庭在应对投资保护的模糊标准(如公平与公正待遇)时只是简单地<br />
对规范标准进行摘要和抽象,并由此确定案件事实是否符合这些标准,而这些对标准的摘要<br />
抽象可能是从先前仲裁庭的类似论述中得出的,这些论述本身就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正当的依<br />
据。 190 尽管这可能符合 ICSID 仲裁撤销委员会近来制定的最低要求, 191 但是在这种模式下<br />
仲裁庭可能无法证明其是如何将公平与公正待遇的抽象解释建立在经过审慎讨论和评价的<br />
法律形式之上的。因此,他们无从反驳的是,他们仅仅是根据仲裁员的主观标准和个人偏好<br />
决定裁决的内容。<br />
第二个问题是仲裁庭在解释诸如公平与公正待遇之类的抽象概念时未能阐明其所作出<br />
的规范性假设,而是通过对法律问题简单地处理,更多地通过断言,而非法律论证和推理,<br />
将自己限制在对案件事实的大量陈述之中。一个例子便是 Eastern Sugar B.V. v. Czech<br />
Republic 案的部分裁决,该案涉及国内有关食糖配额分配法律的变化违反了荷兰—捷克共和<br />
国的双边投资条约争端。 192 该裁决用 100 多段的文字详尽叙述了对违反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br />
提出的申诉的相关事实, 193 但是在并未明确指出该标准的法律意义和规范内容,甚至没有提<br />
及仲裁“先例” 和条约解释的相关渊源(包括相关的国际法学术著作)的情况下,就认定<br />
捷克政府违反了这一标准。该案的终局裁决只是将公平与公正待遇的规范内容置于一个极为<br />
宽泛的框架之中。仲裁庭认为,违反公平与公正待遇“并不仅仅是由于公然和粗暴干预导致<br />
的,也并非每一次法律有缺陷或者一国未能全面正确实施法律时都会引入这一标准”。 194 然<br />
性质并必须受到遵守)。另见同上注, paras. 129-130。<br />
188 Waste Management v. Mexico, 见前注 44, para. 98。<br />
189 Waste Management,同上 paras. 99 et seq。<br />
190 例见 S.D. Myers v. Canada, 见前注 45, para. 134。<br />
191 见前注 180。<br />
192 Eastern Sugar B.V. v. The Czech Republic (SCC Case No. 88/2004), Partial Award of 27 March 2007.<br />
193 Eastern Sugar,同上,paras. 222-343。<br />
194 Eastern Sugar,同上,para. 272。
而,在如此宽泛的框架内作出的裁决是不适当的,因为目前的共识是公平与公正待遇是一个<br />
具有独立规范内容的法律标准, 195 并且鉴于具体化,该标准已经被仲裁裁决和学术论著所接<br />
受。 196<br />
Eastern Sugar 案中的推理类型对仅仅涉及某程序中的当事人的争端可能是充分的,然而<br />
其不符合争端解决机构在公共治理背景下对于推理质量的要求。尽管不能期望仲裁庭对当事<br />
人提出的每一个国际法律问题的先例都进行细致地审查,而且仲裁庭难免受到法律意见书的<br />
质量以及成本和资源的限制,但是如果没有仔细研究国际法渊源,也没有运用一个令人信服<br />
的解释方法,这对界定某一投资保护法律标准的内容来说就是远远不够的。这对于建立在国<br />
际法基础上的仲裁制度以及试图援引先前裁决来论辩的投资条约案件来说是一个基本的责<br />
任。说得更宏观一点,对先前判例的薄弱推理和不充分评价会让人们认为投资仲裁庭是不可<br />
靠的,并且会使仲裁庭适用模糊且不可预料,却完全基于仲裁庭成员个人偏好的法律标准。<br />
同样,尽管投资仲裁庭并不受先前裁决的约束,并且可以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背离先<br />
前的裁决,但是仲裁庭通常应该解释在同一问题上的推理为什么会与先前的著名裁决不一<br />
样。 197 大多数“裁决不一致”的案件中仲裁庭都是这么做的。例如,在 SGS V. Philippines<br />
案中,仲裁庭全面讨论了 SGS V. Pakistan 案的裁决,该案裁决对保护伞条款提出了相反的解<br />
释与适用。 198 同样,在 El Paso Energy v. Argentina 案中,仲裁庭支持 SGS V. Pakistan 案的<br />
方法,而不赞成 SGS V. Philippines 案的裁定,并且深入讨论了为什么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br />
199 而在关于最惠国待遇条款解释的决定中,仲裁庭通常也对其他仲裁庭作出的不一致裁决以<br />
充分说理的方式进行讨论。 200<br />
LG&E v. Argentina 案与 Enron v. Argentina 案的裁决都涉及美国—阿根廷 BIT 项下阿根<br />
廷的紧急立法的合法性问题,这两个案子可能会提高人们对前述问题的关注程度。尽管<br />
LG&E v. Argentina 案的裁决在依照双边投资条约中的实质性义务评价阿根廷的行为时很大<br />
程度上遵循了先前 CMS v. Argentina 案的裁决,但其在必要性抗辩方面与 CMS 案的裁决相<br />
195 参见 Oil Platforms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reliminary Objection, Judgment of<br />
12 December 1996, Separate Opinion by Judge Higgins, I.C.J. Reports 1996, 803, 858, para. 39 (指出:公平与公<br />
正待遇形成了“充满技术性的法律术语,这些术语及其含义在海外投资保护领域众所周知”)。<br />
196 参见 Barnali CHOUDHURY, “Evolution or Devolution? – Defining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in<br />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6 J. World Inv. & Trade (2005) p. 297; Christoph SCHREUER, “Fair and Equitable<br />
Treatment in Arbitral Practice”, 6 J. World Inv. & Trade (2005) p. 357; DOLZER, 见前注 76, p. 87; SCHILL, 见<br />
前注 21。<br />
197 See FRANCK, 见前注 10, p. 1521。<br />
198 SGS Société Générale de Surveillance S.A. v.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ICSID Case No. ARB/02/6),<br />
Decision of the Tribunal on Objections to Jurisdiction of 29 January 2004, paras. 119-126.<br />
199 El Paso Energy v. Argentina, 见前注 186, paras. 71-82。<br />
200 例见 Plama Consortium Ltd. v Bulgaria (ICSID Case No. ARB/03/24),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of 8 February<br />
2005, paras. 210-226。 然而考虑到 RosInvestCo 案中的仲裁庭的推理(见前注 181),这同样并不适用,尽管<br />
这个裁决可能是更有说服力的。See generally Stephan SCHILL, “Most-Favored-Nation Clauses as a Basis of<br />
Jurisdiction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Arbitral Jurisprudence at a Crossroads”, 10 J. World Inv. & Trade<br />
(2009), p. 189; and Martins PAPARINSKIS, “MFN Clauses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between Maffezini and<br />
Plama – A Third Way?” ICSID Review – Foreign Investment Law Journal (forthcoming).
背离。 201 尽管它屡次同意 CMS 案的裁决,甚至引用该案裁决来支持其对于双边投资条约的<br />
实质性义务的解释,包括公平与公正待遇和间接征收概念, 202 但它没有提到,根据国际法<br />
CMS 案裁决关于必要性概念在根本上是不同的。相反,仲裁庭在 LG&E 案中作出了自己的<br />
裁决,没有反驳 CMS 案裁决中提出的反对运用必要性的观点。反过来,仲裁庭在 Enron 案<br />
中又援引并赞同 LG&E 案关于解释实质性待遇标准的决定, 203 但基本上遵循了 CMS 案中关<br />
于必要性抗辩的裁决,并没有采用或提到仲裁庭在 LG&E 案中的矛盾立场。 204 然而,达成<br />
一个投资者和各国都接受的公正的判例的最好办法,就是仲裁庭应以审慎的方式清楚列明其<br />
采用方法和反驳现有抗辩的论据,以达到正确解释投资法与国际法原则上令人信服的结果。<br />
五、结论:国际投资仲裁制度中公共视角和治理视角的规范性依据在操作中存在<br />
的问题<br />
本文认为,国际投资仲裁是全球治理的一种形式。仲裁庭有助于为国家针对投资者的行<br />
为确立适当的标准,并且作为一个审查机构来评价政府在投资者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取得的<br />
平衡。当然,这些仲裁庭受它们所依据的法律的限制,包括作为其设立基础的条约、国家法<br />
律、合同和其他法律文件的规定。它们也是一个规范性法律体制的一部分,该体制包括更广<br />
泛的习惯国际法结构,一般法律原则,以及其他条约和国际决定。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着他<br />
们的工作。但是这些观点并没有详尽说明这些仲裁庭如何行使职责,以及在评价整个国际投<br />
资仲裁制度时的规范性重要事项是什么。<br />
相反,对一个很少被持续考虑到的问题的关注是十分必要的:即现行的国际投资仲裁制<br />
度在什么基础上能具备规范性的正当依据?通说认为它的正当依据是因为它维护了国家促<br />
进投资流动的意愿。如果它确实做到了这一点,那也仅仅是阐述了仲裁庭在履行义务与解决<br />
争端时所具有的一般功能性概念,对于仲裁庭行使更广泛的治理职能来说,其充其量只是一<br />
个无关紧要的理由。而当国际投资仲裁制度作为一种治理形式,它的规范性正当依据便形成<br />
了全球行政法并受其约束,并且很可能与全球行政法职能的某个基本规范概念相一致。对于<br />
监管有效性,社会福利,民主和正义的考虑等都可能包含在这些依据之内。人们对下面两个<br />
问题有可能引发争论:即全球行政法是否应当或是否实际上能够实现切实可靠的承诺,对整<br />
个社会福利或被忽视的经济与社会利益的公平与公正待遇有所促进;或者全球行政法是否应<br />
当更为谨慎地关注如何加强有序的管理和问责性。在考虑了这些影响深远的问题后,可以发<br />
现全球治理行政法包括三个基本规范性概念,且这三个基本规范性概念与作为治理形式的国<br />
201 LG&E v. Argentina, 见前注 135, paras. 226-266; 对照 CMS v. Argentina, 见前注 22, paras. 323-331,<br />
353-394;See for a more detailed comparison of both decisions SCHILL, 见前注 147, p. 265; see also August<br />
REINISCH, “Necessity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 An Unnecessary Split of Opinions in Recent<br />
ICSID Cases? Comments on CMS v. Argentina and LG&E v. Argentina”, 8 J. World Inv. & Trade (2007), p. 191;<br />
Michael WAIBEL, “Two Worlds of Necessity in ICSID Arbitration: CMS and LG&E”, 20 Leiden J. Int’l L. (2007)<br />
p. 637.<br />
202 LG&E v. Argentina, 见前注 135, paras. 125, 128, 171。<br />
203 Enron Corporation and Ponderosa Assets, L.P.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1/3), Award of<br />
22 May 2007, paras. 260, 262, 263, 274.<br />
204 Enron,同上,paras. 288-345. On these cases see Jürgen KURTZ, “Adjudging the Exceptional at International<br />
Law: Security, Public Order and Financial Crisis”, <strong>IILJ</strong> Working Paper 2008/6 , available at :<br />
http://iilj.org/publications/documents/2008-6.Kurtz.pdf。
际投资仲裁具有潜在的关联性。这三个基本规范性概念是:(1)促进民主(2)增强内部行<br />
政的问责性(3)对私人权利与国家权利的保护。 205<br />
第一个规范性概念认为全球行政法的作用是促进民主,但是由于国际投资仲裁作为争端<br />
解决机制所受的实际限制,这可能是一个过于苛刻的系统目标,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投资仲裁<br />
与某些特定的民主问题也会密切相关。显然,许多国家的国内行政法都有民主的要素:它通<br />
过确保行政人员服从法律从而保证他们向议会负责,并通过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程序,保证行<br />
政人员对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团体负责。通过使全球监管的决定和机构更加透明并对国内政<br />
治制度进行更有效地监督和审查,全球行政法的这些发展(其中包括国际投资仲裁庭的工作)<br />
有可能在全球层面上加强代议制民主,并进而促进全球监管决策机构的问责性。 206 这就需要<br />
将一国的行政透明度与问责程序作为投资条约所规定的待遇标准的一部分。<br />
第二个规范性概念是内部行政问责性,其致力于保证以合法性为中心的行政制度(立法<br />
或行政)的下级机关或次要部分的责任,尤其是确保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该概念强调的是组<br />
织与政治功能以及制度的完整性,而不是任何具体的实质规范性,这使其成为一个国际秩序<br />
的潜在模式,尤其成为了一个缺乏实体规范共识的多元化模式。这种观念为一个论点提供了<br />
坚实的基础:即在国际投资仲裁制度机构的工作中应当适用(在适当之处)全球行政法。<br />
第三个规范性概念以自由和权利为导向:行政法律使人们参与行政程序,通过有效地审<br />
查以确保裁决的合法性,以此来保护个人权利和其他市民社会主体的权利。外国投资者的保<br />
护是这个概念的一个实例。这一概念的范围也可以扩大到对国家权利的保护;这个概念即使<br />
在发达国家也可能有助于保护公众与公共利益,但它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于缺乏<br />
政治和经济谈判能力与影响力的弱小国家尤为宝贵。这一概念可能还与另一个观点有部分重<br />
叠:即认为通过确保监管规范的公共性,合理的制定并且公正和可预见的适用监管规范,全<br />
球行政法能够促进法治。<br />
这三个规范性概念对国际组织工作中的合法性与问责性提出了要求。对于国际投资仲裁<br />
庭制度的设计与职能,以及对于其行使治理职能(这是其当前任务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时自<br />
身的合法性来说,它们都具有直接的影响。<br />
在证明国际投资仲裁制度的正当性时考虑这些规范性概念的潜在影响是富有成果的:特<br />
别是这些规范性的概念为其制度设计和实践设定了具体条件或提出了具体特点的要求。同时<br />
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对于要求投资条约仲裁根据其多层次职能行使权力所用的方法应达到绝<br />
对有效和完全合法来说,结构上和制度设计上的问题目前还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些监<br />
管机构必须立即:(1)对特定当事人之间的实际争端进行仲裁并加以解决,(通常是事后的,<br />
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争端双方之间积极的经济关系可能在仲裁时还在持续);(2)秉承法律公<br />
共性的理念,对这些同样的争端进行裁决:即对与特定的政治经济问题和实质的法律标准问<br />
题有关的所有公共权力进行阐述;以及(3)通过对国家和其他主体具有潜在影响的方式解<br />
释适用的标准,并以此进行监管。这就引申出了根本改革的建议,例如,学者 Gus Van Harten<br />
认为应当抛弃他视为私有化治理的现有模式,而创建一个拥有终身制法官的公共机构,即一<br />
205 关于国内行政法律中的类似的规范性概念,参见 Eberhard SCHMIDT-ASSMANN, Das Allgemeine<br />
Verwaltungsrecht als Ordnungsidee, 2nd edn. (2004)。以下段落引用了 Benedict Kingsbury 和 Richard Stewart<br />
关于全球行政法的共同研究成果。<br />
206 在全球监管制度层面上,全球行政法的体系也可能有助于协商式民主的发展,尽管此概念的要素及其有<br />
效实现的条件还没有得到解决。参见 Robert HOWSE, “Transatlantic Regulatory Cooperation and the Problem<br />
of Democracy” in George A. BERMANN, Matthias HERDEGEN and Peter L. LINDSETH, eds., Transatlantic<br />
Regulatory Cooperation: Legal Problems and Political Prospects (2000) p. 469。
个常设的国际投资法庭。 207 但从实际来看,成立这样一个机构或上诉机构,在短期内不太可<br />
能实现。因此,相关主体在现有的制度内而非在其之外争取更多的合法性,既是必要的,也<br />
是更加可行的。这一直是本文的分析和一系列相对温和建议的重点所在。<br />
对于公共视角和治理视角的制度设计以及仲裁推理来说,存在一个基本的结构性问题:<br />
当事方,尤其是投资者,可能对所需作出的努力,特别是对支付公共产品的成本不感兴趣,<br />
这些公共产品包括对国家行为的事前治理,以及通过事后仲裁对公共利益与投资者利益进行<br />
复杂的平衡。因此,这样的公共产品的供应是不足的。此外,大部分投资仲裁制度也没有任<br />
何税收和国家捐赠的一般制度提供资助。即使国际投资仲裁中存在可能危及其可行性的过度<br />
扩张或缺乏合法性的系统性问题,但这是集体行动上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投资者,也几乎<br />
很少有被告国,愿意支付费用来解决这一问题。 208<br />
一些仲裁员或仲裁小组可能能力很强,即使没有经济报酬,他们也积极地为某些特定裁<br />
决作出了额外的工作。但是,很多仲裁员在没有额外报酬时并不必然愿意承担较大的责任,<br />
而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可能确实会对那些将案件置入到更多考虑因素中的仲裁员产生担忧,并<br />
且担心仲裁员的任命程序在某种情况下可能导致不匹配和怪异的组合。机构性的支持,如由<br />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秘书处或其他仲裁机构提供的支持,在解决更大范围的问题时能有助<br />
于提供推理,特别是如果其官员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并有着系统层面的视角的话。然而,这种<br />
机构支持的有效性因为机构和其他因素的不同而千差万别。<br />
这个问题由于提交国际投资仲裁庭的案件范围的不平衡而更加严重。除非在极其特殊的<br />
情况下,这些案件都是以国家为唯一目标。虽然公益组织不会或者还没有因这些案件对国家<br />
提起诉讼,但是可以想象,如果他们找到解决成本的方法,非政府组织可能成为投资者并通<br />
过仲裁挑战国家行为,这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在国内法院对外国提起诉讼、或者其他一些非政<br />
府组织通过多年来购买公司的股票以试图影响公司行为的方式是一样的。 209 因此,往往是只<br />
有与案件结果有较大经济利害关系的投资者才会提交这些案件,并且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得到<br />
直接的经济利益,而非就新的问题产生新的判例或提高推理的质量。此外,在一些案件中有<br />
正当和重要诉求的投资者根本不会提起诉求,因为他们不希望被排除出相关市场。小投资者<br />
们则可能因为国际投资仲裁所需的巨大成本而放弃提出他们的诉求。 210<br />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在制度设计及其产生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上与国际人权法庭等<br />
机构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在诉讼资格上设置了一些限制,并通常需事先用尽合理的当地救<br />
济,但他们对于声称自己为实质性受害者的人来说是开放的,并且成本相对合理。 211 世界银<br />
207 VAN HARTEN, 上注 7, p. 180 et seq。 对于国际投资仲裁作为一个审查东道国主权行为的机制的适当性<br />
的类似质疑,见 Vicki L. BEEN and Joel C. BEAUVAIS, “The Global Fifth Amendment? NAFTA’s Investment<br />
Protections and the Misguided Quest for an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Takings’ Doctrine”, 78 N.Y.U. L. Rev.<br />
(2003) p. 30; Marc R. POIRIER, “The NAFTA Chapter 11 Expropriation Debate Through the Eyes of a Property<br />
Theorist”, 33 Envt’l L. (2003) p. 851。<br />
208 在投资者的诉求是基于善意提出时,对提出有一般重要性的特定类型案件的资助方法可能是:将仲裁成<br />
本转移给国家一方。参见 SCHILL, 见前注 169, p. 653。<br />
209 但是参见 Luke PETERSEN and Nick GALLU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y Protection of<br />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s”, 10 Int’l J. of Not-for-Profit Law (December 2007) p. 47, available at :<br />
www.icnl.org/knowledge/ijnl/vol10iss1/ijnl_vol10iss1.pdf,(讨论了非政府组织的投资条约的保护与其在外国<br />
领土的活动)。<br />
210 其次,成本转移技术对于高成本的阻碍影响可能提供一个解决方法,参见 SCHILL, 见前注 169, p. 653。<br />
211 通常他们并不支付机构本身的费用或者国家辩护的费用,并且可能有非政府组织或者公益律师能够并且
行以及其他国际开发银行的检查小组也与此类似。在世界贸易组织体制下,由于公司或其他<br />
私人主体缺乏直接提起诉讼的权利而限制了世贸组织的受案范围,但在国家间的诉讼程序<br />
中,1994 年成立的由七名成员组成并且能产生更多先例的常设上诉机构,部分地解决了<br />
GATT 专家小组在法律发展过程中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结构性问题。 212<br />
现行体制下的投资仲裁庭是一个高度分散和碎片化的监管机构。尽管个人对仲裁庭的多<br />
重任命会对其产生一些松散的监管,但这通常并没有将其很好的置于一个统一的机构中。此<br />
外,诸如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银行和与贸易有关<br />
的投资措施 WTO 专门委员会等组织都对外国投资理论和政策提供了一些制度监督和专家意<br />
见。通过仲裁庭自身对于先例及共同方法的运用,通过政府间组织对其出版物和投资法律培<br />
训(如 UNCTAD,或者 OECD)的提炼和传播,以及通过非官方主体,如仲裁大会或者对<br />
判例、现有或拟议的条约条款进行分析的学术评论家,一些知识统一体在此基础上得以建立。<br />
但总体来说,与 WTO 争端解决机构,甚至与 OECD 的监管机构(如根据《经合组织关于反<br />
对在国际商务活动中贿赂外国公务人员行为的公约》而设立的反贿赂工作组)相比,仲裁庭<br />
很少能被置于有助于实现治理目标的政府组织之中。投资仲裁庭对国家有非常大的监管影<br />
响,但是又缺乏能有效纳入仲裁庭的政府间政治组织,这两方面的结合增加了获得高质量推<br />
理和形成良好国家管理标准的知识的成本。国际投资仲裁庭认为,它们既是全球行政法的制<br />
造者,又是全球行政法的对象,这种认识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正在迅速地发展。<br />
渴望以优惠的条件代理他们的案件。<br />
(编辑:袁屹峰)<br />
212 有关综述,参见 Joel TRACHTMAN, “The Domain of WTO Dispute Resolution”, 40 Harv. Int’l L. J. (1999)<br />
p. 333。